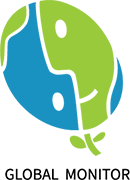去年10月16日,德國的團體舉辦了一場工作坊,讓來自中國的朋友和德國工運朋友交流。在這個科隆工作坊上,有三個青年(兩個德國人,一個瑞士人)分別介紹了他們的鬥爭經驗。
不來梅賓士汽車廠的工人鬥爭
位於德國北部的不來梅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市區以北65公里的不來梅港位於北海入海口,為德國第二大港。不來梅市有50萬居民,接近不來梅港口的區域另有居民10萬人。1985年,該市與中國大連結為“姐妹城市”(即友好城市)。除了港口、造船、漁業和食品加工等傳統產業之外,不來梅市最重要的兩個支柱產業是汽車製造和航空航天。該市的賓士汽車廠規模屬德國第二,供應全球四分之一的賓士轎車。來自該廠的年輕工人Noni講述了該廠及當地工人的鬥爭動向。
Noni,不來梅賓士汽車廠工人
不來梅一方面靠工業生產,另一方面靠港口貨運。在這些行業裡,五金工會占主導地位。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在不斷削減,汽車出口的情況還好,但正式工人日益減少,臨時工則不斷增加。我們經歷了這一改變。而在企業改組過程中,工會站在資方立場上支援這一進程。而就是這樣的傳統工會,也只存在於賓士的3家工廠裡。其他如派遣工等都是沒有組織起來的。
我先是在賓士實習,現在正式在生產車間工作。作為對工會感興趣的青年,我參加了工會培訓。受到的教育是:“我們應該自我組織起來!”而其實在生產線上,工會根本不起作用,只不過是跟公司管理層共同管理生產罷了。過去,在許多大公司裡,都發生了工人的大規模行動,包括反對工會的行動,因為工會認可資方的裁員方案。我們公司也是如此。
因此,我們建立了自己的工人委員會,並且在鬥爭中認識了港口的其他工人,開始與他們聯合,前往拜訪他們。我們互相支援,發出倡議:我們要獨立于工會,自行組織起來!9個月前,我們嘗試組織起不同公司的工人代表,這樣各廠工人——包括港口,醫院,汽車行業的工人——便可聚集起來,交流思想,交換經驗,共同教育和建立聯繫,不管來自什麼行業。
我們每月定期會面,討論各種不同的主題。我們有這種訴求,因為大家——不論正式工還是臨時工、派遣工——都意識到工會不代表工人利益,所以建立一個自己的新工會的呼聲很高。我們的呼籲收到很好的效果。
由於我們不是在大型活動中認識的,沒有公共平臺可供工人們彼此瞭解,而是在鬥爭中私下認識的,有很大偶然性,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創立了自己的網站,並在感興趣的工人之間建立聯繫。我們的另一個想法是,與普通的基層勞工一起組建自己的工會,希望有自己的鬥爭能力並向公眾宣傳我們的想法和需求。當然,我們不願像傳統工會那樣變成行政管理的一種工具。
我的另一個想法是建立工人的國際聯合,也就是能夠跟國際上的其他工人建立聯繫。這個想法還比較抽象。不過,我們賓士廠也直接面對著可能把工廠搬到中國去的問題,是不是我們應該跨國界聯合呢?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IWW)[1]早年的想法如果能成功,那多好啊。目前我們的想法是加強聯繫,形成自己的組織。
派遣工越來越多,他們沒有受到相應保護,但要組織他們難度很大,因為派遣工都是在這裡幹一段時間後就被派遣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也可以隨時解雇。他們關心的是如何得到一個比較穩定的工作崗位。隨企業“轉型”而大量產生的派遣工和臨時工,主要就是年青人。就我們所在工廠的情況來說,廠裡工人的平均年齡47歲,老工人很多。基本上,廠裡每年會招100名年輕人進來,這些剛進廠的工人不能立即進入生產線操作,需要學習,這點很有利,我們有充足的時間來組織他們。我的同事有一半都參加到我們的組織裡來。要想聯合青年一代參與勞工運動,最重要是必須瞭解青年們的生活狀況,不是泛泛地談論理論及遠大理想。三、四十年前,有很多年青人投入組織工人的工作,積極關心工廠裡的情況,但現在就不同了。目前的反法西斯反種族歧視吸引了很多青年人。不來梅的情況比較例外,青年再次表現出對工人狀況的關心。老一代的問題是:如何發動年輕人來關心工廠裡的問題。
為什麼工人不信任工會?在德國,法律上對工會的定義是:工會是企業的“社會夥伴”。工會官僚當中盛行一種說法:“舉行一次罷工是容易的,難的是怎麼結束它。”(即如何操縱和控制工人鬥爭以達到勞資“平衡”——作者注)隨著企業“轉型”,工會越來越不重要,顯得多餘。經濟發展的進程使雇傭關係變得越來越不穩定,而工會都站在政府和資方一邊,沒有別的選擇。
我談的是如何處理勞資關係。有人提到階級衝突和決戰問題,我希望這種決戰最好不要發生,或者應當盡力避免,最好是制度自身能把它化解掉。我覺得我們一定要積極主動,使之能夠掌握在我們手裡。舉例說吧,在伊朗和希臘,雖然鬥爭艱巨,曠日持久,但最後都沒有成效。所以我覺得在全球化經濟下,鬥爭很困難。我們講述我們的鬥爭,因為跨國的交流很重要。我想,這就是盧森堡所說的社會主義還是野蠻主義的問題,這是核心問題……
FAU——新聯合工會的嘗試
一方面,德國工人受到資產階級和政府的不斷進攻,另一方面,工會、企業委員會之類的組織普遍官僚化,持親資方、親政府立場,漠視工人利益。因此,一些力圖進行抗爭的工人和工會正尋求摸索新的工人組織形式。FAU是其中一例。來自柏林的FAU組織的成員介紹了該組織的情況,具體講述了柏林巴比倫電影院的罷工事件和該組織面臨的困境:
來自柏林的FAU組織成員
FAU是一個工團主義的企業工會聯合會,是受到工會支援的、自下而上實施基層民主的工會。最初的想法來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工團組織的觀點。
在德國的多個城市,都有工會組建的FAU。它們不想帶上宗教及黨派色彩,也不願意跟政府走得太近。它們要在日常鬥爭中互助,而非期待外援。它們要求改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以及在多個領域裡有參與之權。目的是通過團結起來改變生活及社會,最終戰勝資本主義。
在實際操作中,FAU組織從事説明工人提高工資等等非常實際的鬥爭,也有許多國際行動,比如支援西班牙的其它姊妹組織。FAU還組織集體性的、影響力大的罷工,比如柏林的巴比倫電影院的罷工。
這是柏林唯一接受國家資助的一家電影院。因為其老闆跟左翼黨領導層的關係很好(雖然老闆本人不是黨員),所以得到資助。電影院與左翼走得很近,經常上映批評社會的電影,可惜電影院員工的待遇卻跟它所宣揚的“社會主義”相去甚遠。
2008年底,員工們說,工資、工作條件以及老闆對待員工的態度,讓我們沒法忍受。他們起先要求組建企業委員會,但發現效果很差,因為企業委員會權力有限,無權將員工組織起來,於是意識到需要工會。他們向威爾第(VER.DI)服務行業工會發出求助信,但沒有得到回應,他們提出的問題也從未得到答覆。員工們的理解是,老闆看來跟VER.DI的領導層也走得很近。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找到FAU(此前半年,FAU曾培訓並幫助他們中的一個員工,幫他找到律師協助)。FAU派出一個企業工作小組,與員工們一同向老闆提出訴求。企業工作小組定期跟員工開會討論,把訴求寫下來,形成集體合同的初稿,將之交給老闆。老闆壓根不搭理。矛盾激化了,勞資關係達到緊張狀態,最後矛盾公開化了。員工們組織起來,派發傳單,最後封鎖了電影院。壓力通過領導層傳遞到了左翼黨派那裡。2009年9月之後,VER.DI工會終於介入,通過媒體表示願意幫助電影院的員工跟資方簽訂集體勞動合同。資方則提出訴訟。法院判決結果是,FAU可以在電影院組織員工罷工,但無權在行業裡簽訂集體合同。2009年12月,判決由FAU支持成立的工會是沒有法律效力的。2010年1月,VER.DI與資方簽了集體合同,條件遠低於員工提出的要求,並且不能適用到整個行業。2010年我們又打了一場官司,至7月裁定勝訴。FAU幫助組建的工會獲得承認;但工會雖然合法了,卻沒有與資方簽定集體合同等權利,也不容許集體上訴。因為按照德國法律的規定,只在一家企業裡存在的工會不具備全行業工會的能力,同樣,只在一家企業裡訂立的集體合同不能推行到全行業。這事實上意味著企業工會無權罷工,就法律來說,德國工會受到的限制比美國和中國更嚴重。
總之,在現行法律規定中,FAU沒有成立工會及簽訂集體合同的權利。
現在,FAU工作小組雖然在電影院活動,其地位得到加強,但員工都換了,老員工的待遇有了改善,新員工不願鬥爭。我們認為,鬥爭並未結束,也沒有徹底失敗。
至於VER.DI工會,經過這場鬥爭之後,在電影院行業已難以立足。而隨著放映技術數位化的發展,現在的影院模式已經變了,推入一張CD碟片便可放映。以我的悲觀想法,這樣一來要實施集體合同就越來越難了。
瑞士“為社會主義而行動”——爭取移民居留權組織
在10月16日召開的工作坊上,來自瑞士的客人大衛(David)團體講述了他們的活動,這不僅使來自中國,而且讓德國的工運份子也有機會瞭解在這個鄰國發生的事情。該團體名為“為社會主義而行動”,是一個為外籍移民工人的居留權而鬥爭的左翼組織,分別在瑞士和德國行動。以下是大衛的介紹:
“我來自瑞士巴塞爾的‘為社會主義而行動’組織。我們這個組織有許多積極份子,努力為非法移民瑞士的人爭取居留權。瑞士政府一直想要阻止我們組織的行動。在瑞士,除了正常居民計780萬人口之外,還有20~30萬人沒有合法居留證件。瑞士法律規定,‘難民’有10種不同的居留許可證,待遇和權利各有不同,非常複雜,包括在哪裡居住、得到政府的保障和補貼都各不相同。團體在工作中要面對的另一個困難是,政府讓難民們每星期更換居住地,使得團體難以接觸移民。
“非法居留的移民在跟團體接觸時面對的問題有:語言溝通方面的困難;很多人對自己的狀態很恐懼,政府很可能會把他們送進監獄,或暴力驅逐,例如被捆綁在飛機座位上強制遣送回國等。怎麼把他們組織起來是個很大的難題。
“我們的做法就是在很多城市建立小的支部,到他們的居住場所做宣傳,告訴他們我們能提供一些幫助,讓這些移民知道在瑞士有些小政治團體會幫他們。比如說前段時間在瑞士伯恩跟他們見面時,我們親自去接他們,這是個很大的挑戰,因為他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有可能被檢查證件,並有可能被抓。
“我們最主要的一個工作重點,就是使他們的身份合法化,包括:1、要求讓這些移民享有合法居留的權利;2、要求讓他們的家人能來共同居住,即申請家人來瑞士團聚;3、享有工作的權利和社會保障的權利。
“今年夏天,我們組織了這樣一個活動。我們佔領了瑞士議會附近的一個小花園,設下帳篷,組織了為期7天的靜坐、集會,有二、三百人參加了這個活動。我們每天舉行兩次全體大會,用7種語言說話,讓與會者知道我們討論什麼議題,以及如何把問題和要求傳達到議會去。不合法的人(即無證移民)以不合法的方式佔據公園集會,這種方式造成了很大影響。這期間,我們組織了多次示威遊行,前往聯邦機構附近,以及到頒佈有關難民法令的機構去遊行。這7天裡,我們的行動有明確的分工,包括建立負責安全的小組,24小時從事保衛工作,以避免被襲、被盜等事件,小組由持有合法居留證件的瑞士人組成。
“2008年我們搞過一次類似的行動:佔領教堂。瑞士很少發生罷工、遊行,所以我們佔領教堂和公園的行動引起社會很大的關注。
“我們團體以及‘難民’的內部也有分化和分裂。有的人是出於政治原因來避難的,有的是出於經濟目的而來。前者比如伊朗‘難民’,他們說:我們跟非洲來的難民是不一樣的。許多人則認為瑞士人歧視外國人,因此政治上的保證更重要。我們認為政治和經濟上的利益是可以結合的。再拿我們搞的為期7天的活動來說吧。當時很多有合法居留權的瑞士人也來參加,支援這一行動,但之後他們可以回家過正常生活,‘難民’們卻要長期生活在惡劣的環境中。這也是分化的原因之一。語言問題是個障礙,我們要做7種語言的翻譯工作,而且‘難民’因此難以跟媒體溝通。不過,召開全體大會時,我們鼓勵‘難民’們自己組織話劇演出等活動,鼓勵他們自己主動積極地起到領導作用,收效比較好的。
“假如‘難民’不接受政府安排的遣送的話,就要坐2年的牢(瑞士加入歐盟後,改為一年半)。瑞士政府對待難民比較嚴苛,針對難民的標語、宣傳都很極端,因為自我保護之故——瑞士的經濟情況比西班牙、義大利等國要好。前段時間,有一個難民被遣送回國的時候,被捆綁在飛機上,結果在遣送過程中死去。政府給這類遣返者提供的是普通飛機票,被遣返者的手腳都用繩索捆綁起來,再戴上面具,所以會因緊張而導致吸呼困難。官方說,這樣做是為了防止難民以自殘的方式要求延長居留。為此我們計畫搞一個行動,阻止飛機起飛,同時告訴被遣返的‘難民’不要上這個飛機,否則會有生命危險。
“對我們來說,為居留權而抗爭是‘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一部分。”
[1] 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IWW),1905年6月由美國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激進工聯主義者共同創立的工會聯合會。其目標是:不分性別、種族和技能,把所有產業的所有工人組成“一個大聯盟”。他們反對與資本家妥協,呼籲採取“直接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