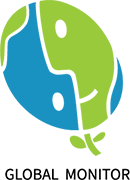2009年 4月 26日
Chris Jones
按:作者是英國利物浦大學社會政策和社會工作教授。文章指出社會服務的對象絕大多數是窮人,他們處於社會最底層,處處受排斥。文章回顧了傳統社會工作的理想主義傳統怎樣理解貧窮現象,二戰後至七十年代根據這種觀念所推行的社會工作實踐的局限,並在最近二十年新右派(作者認為新工黨的第三條路線不過是新右派的變種)執政下社會工作價值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文章最後部份提到英國前線社工普遍陷入困境,有深深的無力感,讀來就像談論本地社福界的現況。Chris Jones認為貧窮以及由此伴隨著的歧視和社會排斥,源於資本主義下面的不平等。如果這種「社會階級分明的結構」仍然不受挑戰的話,很難對社會工作前途感到樂觀。
有興趣進一步閱讀的朋友,可參考Chris Jones的兩本著作《國家社會工作與勞動階級》(State Social Work and the Working Class , 1983 , Palgrave Macmillan)及《貧窮、福利與懲罰性國家》(與Tony Novak合著 Poverty, Welfare and the Disciplinary State. London ,1999 , Routledge)。後一本書好找,前一本恐怕要到大學圖書館才能借到。
英國的社會工作和其他地方一樣,埋首於貧窮和社會排斥問題。使用社會工作或在強制下獲得社會工作幫忙的人,絕大多數是窮人,來自人口結構中最弱勢的階層。儘管社會描述或認知貧窮的方法隨著時間改變,這種情形卻不曾變過。根據北美社會學家Alvin Schorr(1992,p.8)的觀察,
「接受個人社會服務(personal social services)的案主最顯著的共同特色是貧窮和被剝奪。或許咸認社會服務應該建立在普世原則上的緣故,通常這個特點沒有人會提起(Often this is not mentioned),只是在這一行裡大家心照不宣罷了。一項又一項的調查顯示,案主都是失業的人,或嚴格來講,就是沒有受僱——目前沒有工作,也沒有去找工作的人。或許其中有半數領政府的收入補助(income support),但收入僅及補助標準或在標準之下的人多達百分之八十。(黑體字乃編者所加)」
社會工作案主如此明顯的人口特色居然通常略過不表(not mentioned),十足透露社會工作與窮人的關係,以及英國社會工作做為國家處理窮人問題機構的獨特,甚至怪異之處。社會工作儘管處理窮人問題,卻似乎不肯承認這個中心事實。然而,通常是貧窮及隨之而來缺乏社會政治影響力與資源兩者結合的結果,破壞了社會工作案主的生活與幸福,削弱他們料理事情的能力——不管是孩子的、伴侶的、衰老的事情或疾病。就這方面來說,切記貧窮從來不單指物質資源匱乏,雖然這點也很重要;誠如Novak(1995)所言,它也指一個人和社會的關係;亦即他/她的身份和地位。在英國這樣的資本主義社會,我們甚至能夠更精準的指認這種關係的某些關鍵特色,在英國,貧窮一般指社會地位低下、貧窮權力、生活選擇受限,以及一大堆在住屋、教育、就業、健康和休閒等方面的不利條件。這些不利因素又互相糾結成一張網,讓人格外難於掙脫,英國社會階級分明的結構已持續存在兩個世紀以上,就明明白白反映了這個現象。如果再結合其他形式的系統化區隔,諸如「種族」(race)和性別,貧窮的後果變得更加悲慘(Becker and MacPherson, 1988)。
這些後果非常明顯,許多社會工作者知之甚詳。我們還有各式各樣豐富的研究資料,詳述貧窮及不平等對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的人造成的衝擊(請特別看Wilkinson, 1996)。例如,你很可能比和你同齡但地位較優越的人短命,你的子女有較大風險碰到重大疾病或意外,你比較可能得癌症和心臟病,讀最差的學校,住最惡劣的社區,做最低賤的工作——如果還找得到工作的話,此外還得忍受別人堂而皇之對你的生活和人品極盡誣衊之能事。簡而言之,這就是社會工作的環境。從它的起源,維多利亞慈善組織協會(Victorian Charity Organisation Society, COS)開始,現代社會工作(有別於更早形式的施捨救濟)一直以特定階級為對象,而非普渡眾生。它尤其關注社會中最窮的人的生活。本章大略討論社會工作這個行業如何愧對窮人,而在減輕貧窮對社會最弱勢者的衝擊方面,成就又是如何乏善可陳。
正視貧窮問題
要弄清楚社會工作與貧窮的關係,必須先了解社會工作一直想把服務對象所面臨的問題,解釋成主要是個人和家庭缺陷造成的,而非根源於社會操作和運轉方式。這種保守的解釋法,加強了資本主義社會繁殖貧窮與不平等的基礎,並把焦點轉移到窮人的性格、品德和生活方式,而贏得可觀的支持,尤其受社會菁英歡迎,後者為了合理化他們所享的特權,遂將特權歸因於他們自以為高人一等的能力才智。社會動用了相當大的努力和資源來鞏固這種觀點,有很長一段時間訴諸宗教,晚近則祭出社會科學來支持它和自圓其說。在如此睥睨的眼光注視下,窮人的弱點被抓出來解釋為什麼貧窮的根源在窮人自己身上(Murray, 1990有極佳的闡述)。同時,資本主義被吹捧成人類所可能找到的最佳社會經濟制度,最可能增進廣泛人類福祉。自蘇聯帝國在二十世紀將結束之際解體以來,資本主義絕對優越論愈發甚囂塵上。
在這場關於現代社會貧窮的成因和特性的持續爭論中。社會工作只不過是眾多出於保守派思維模式(conservative paradigm)的國家福利措施和活動之一(Jones and Novak, 1999)。然而,在龐雜的國家福利服務中,社會工作地位獨特,它一直和社會中最貧困的人打交道,因此提供了一個特別有利的觀察位置,可供探究此種意識形態的發展和實踐方式,以及社會工作如何既反映又促成社會對貧窮的普遍看法。當資本主義社會試圖解決貧窮問題,而不只是限制或約束窮人時,會遭遇困難和壓力,社會工作往往首當其衝,尤其是法定部門的社會工作。下面我們將討論,社會工作試圖「解決貧窮問題」(do something about poverty)的野心,有時造成它與廣大福利體制及國家整體的關係多少有點扞格(problematic relationship);有些機構傾向於用嚴懲及污名化的辦法去對付像社會工作案主那樣,一般認為不具經濟和社會價值的人,社會工作跟這類機構的摩擦特別多。
把窮人視為麻煩
在現代英國社會工作史上,創立「慈善組織協會」(COS)的先驅者地位特別重要,因為他們設定了這一行的主要工作原則。有意了解社會工作發展的人應該特別注意Charles Loch(1904)、Bernard暨Helen Bosanquet(1914),以及Octavia Hill(1884)的論述。儘管他們的觀念和政策主張並未完全實現,但他們對英國社會政策的影響歷久不衰,足以和Beatrice及Sydney Webb等人相提並論。他們的論述思想縝密、立論嚴謹,奠定社會工作後續理論和實務發展的基礎大要。他們對社會工作看法的重要理論支柱,來自理想主義派哲學,Bernard Bosanquet(1895)是此派在十九世紀尾聲的領導人物。簡單說來,這一派哲學主張道德(包括想法、價值和人格在內)高於一切,決定了人在社會的地位和幸福(well-being)。它並未完全忽略諸如環境衛生和適當居住條件等更廣大社會因素對個人福祉的影響,但相較於唯物論者主張結構問題高於一切,及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的性質本身造成貧窮困苦的論點,理想主義者卻認為性格才是主要決定因素。他們的立場清楚呈現在COS月刊這一段文字裡:
無庸置疑英國勞動階級的貧窮不是環境造成的(因為他們的環境好過歐洲任何一國的勞動人口);貧窮是因為他們的習性只管眼前、不顧將來且不如節儉。
他們如果想富裕起來,就必須徹底洗心革面、自我約制和多為明天著想。(Charity Organisation Review, 1881, vol.10, p.50)
對這些社會工作先驅而言,勞動階級窮人的貧窮和匱乏,不是物質資源不足所致,而是這些人的品德不好;在他們看來,改變窮人的個性(和行為),是解決貧窮問題的唯一方法。COS第二十三次年度報告(The 23rd Annual Report, 1891)簡明扼要地概述了此一觀點:
大體說來,做完一切該做的推理之後,我們可以這麼說,性格決定命運;因此,要永久改變命運就必須從性格著手。能夠從外在去改善命運的事當然要做,但不去改變內在,效果不會持久。
COS的理想主義觀點不僅解釋貧窮困苦的原因,還指引干預和工作的方向。畢竟社會工作不只是一個解釋貧窮的行業,它還是一種社會行動:解決貧窮和人類苦難。社會工作決心採取行動,因為它相信窮人有救,可以提升到對社會發展有益和有貢獻的地步,這也是社會工作被視為自由派和人道主義的部份來由。更保守的看法則主張,絕大多數處在社會體系底層者,之所以在那裡,是因為他們有生物上的缺陷(flawed biology)(這種特別惡毒的意識形態,一直靠種族歧視延續生命,最近又利用「下層階級」「underclass」的概念借殼上市),因此不能也不該替他們做任何事;社會工作與之相反,雖然附加了一些重要的條件限制,但傾向於在保守架構裡面(within)提出比較樂觀的看法,認為窮人還是「有救的」(redeemable)。近幾年來,尤其歐洲和美國新右派政府上台之後,此一較樂觀的看法備受攻擊和污辱,指責它對待最貧窮的人過於軟弱,養成社會工作案主的依賴心(Cannan, 1994/5)。
個案工作和社會民主
現在回顧起來,我們可以看到依照COS先驅當初構想設計的所謂古典社會工作,在社會民主時期成果最為豐碩,那段時期在英國維持了大約三十年,從1945年到1975年。當時主要政黨及一般菁英大致有個共識,認為社會工作可以也應當發展成一種國家行動,理由是家庭個案工作能夠有效減少貧窮,尤其隨之而來的家庭破碎、疏忽兒童和青少年犯罪等諸種社會問題。引用佛洛伊德心理動力學派(psychodynamics)的觀點,社會工作將自己定位為致力於改造人口中那百分之十似乎困在貧窮絕境者的那種(the)社會策略。那些人被形容為「問題家庭」(problem families),即使促進充分就業和大幅擴充國家福利的凱因斯經濟政策在1948年後付諸實施,他們被認為還是沒有能力從進步中獲益。此處可以看出社會工作的理想主義漸趨成熟。社會工作理論家和實務工作者大言不慚地宣稱社會工作可以帶來持久轉變(這個主張從未實現,後來反彈回來成為攻擊這個行業的口實),自稱已掌握個案工作的工具與知識,可以持久改變最貧窮者的性格和道德。他們仍堅持保守派思維模式,把最貧窮者的問題歸諸於性格和道德,尤其關注勞動階級的母親,認為社會工作只要干預這些家庭,並和這類母親建立密切關係,便可以促成持久的內在(internal)改變,達成COS先驅衷心嚮往的目標。英國社會福利在1945年後擴充,此時社會工作的理想主義,加上它強調的貧窮文化及貧窮與剝奪因果循環的說法,獲得廣泛支持。即使如此,還是要等到1970年代初期,社會工作才有自己的國家機構,由地方政府社會服務署負責(在蘇格蘭是社會工作署),這多少透露社會工作或許從來不曾得到全心全意的支持。左派方面,有些人相信,遭受最嚴重剝奪的人需要更好的救濟,而不是社會工作;右派方面,包括國家刑事司法體系內的很多人,則反對社會工作的自由派作風,認為它對案主太軟弱,造成他們對福利的依賴。
在1945年後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裡,社會工作深受佛洛伊德學派影響,處理貧窮問題時採行一些不近情理的措施,雖然從理想主義的架構來看,這些措施完全可以理解。從案主的立場來看,當他/她發現自己的貧窮和種種隨之而來的困苦,現在被視為僅只是更深層心理問題的表象,一定會困惑不已。貧窮的本身(per se)不是問題,有問題的是「家庭關係裡的暗潮」(deeper disturbances in family relationships)(Rodgers, 1960, p.89)。一如Helen Bosanquet一個世紀前的主張,社工員中頗有些人認為,案主遭遇困難和痛苦不是因為他們缺錢,而是因為情緒困擾使得他們亂花收入(Smith and Harris, 1972)。
這種觀點意謂著社會工作實務傾向於把社會問題當個人問題處理,而且淡化案主生活中物質匱乏的冷酷現實。更確切的說,它把物質救濟,尤其是金錢援助,當做應急的最後手段,僅在情況危急到可能威脅眼前個案工作關係時才使用。在各式各樣心理學概念層層包裹下,社會工作處理物質援助時,往往對案主極盡刁難之能事,即便決定發放,也是在嚴密監督下為之。這種措施如今已在社會服務機構根深蒂固;目前各機構的普遍做法是,盡可能避免發救濟金,改為發福利券(vouchers),並限制在指定的折價商店使用。當然,發福利券總比什麼都不發好些,但對案主來說,這終究是一種羞辱和鄙視的幫助形式,擺明了他們是沒有用的人,和社會大眾不同。此外,福利券和其他形式的國家救濟一樣,需要辦各種申請手續,連這麼一點微薄的援助都需要申請,此事本身即可能是一種羞辱,進一步損傷案主的自尊心。坦白說,這實在是很無禮的福利。
窒礙難行的策略
純粹就理論來說,社會工作希望透過個案工作關係,把案主矯正過來,變成品行端正的公民,有孩子的家庭尤然。社會工作從來沒有妄想過憑這種方法可以徹底消滅貧窮,但它確實相信個案工作能夠幫助貧困家庭用比較不反社會的方式面對貧窮,或能夠灌輸他們正確的看法和價值觀,以確保他們的孩子不會誤入歧途及養成所謂的寄生行為(如長期依賴社會福利),進而可能成為有用的,能自食其力的人。經驗卻證明這種策略窒礙難行(以它對貧窮和窮人的保守定義,這個結果在預期當中)。
困難很多。一方面,社會工作不受窮人歡迎。自有社會工作以來,勞動階級的窮人始終普遍抗拒社會工作干預,抵制社會工作對他們的貧窮困苦擺出鄙視、高度干涉和說教的態度。漸漸地他們變得害怕社會工作,因為社工員取得更多法定權力,可以在干預無效時把孩子和其他人從家庭帶走。許多案主和潛在案主對社會工作似乎有一種觀感,認為社會工作是問題的一部份,而非解決方案的一部份。例如,根據種族平等處(Race Equality Unit)處長Ratna Cutt(2000, p.28)的報告,「黑人社區對社工員的認知是,只要和社會照顧機構有任何瓜葛,結果一定對黑人不利」。
另方面,個案工作法本身也有一些內在的困難。從它的實施環境來看,這種方法有些不切實際。治療關係(therapeutic relationship)本來就夠難建立了,如果參與者再心不甘情不願的話,更是難上加難(大多數案主不是自願前來接受社會服務機構治療,而是經由第三方轉介,通常是由其他公家機構送來,如法院、警方、家庭醫師、保健員或學校)。然後還有社工員和案主的權力差別問題,這使得雙方關係非常不平等,不管他們原來的社會和階級差距如何。Bryan與同僚(1985)以居住英國的黑人婦女為對象,作了一項很有份量的研究,報告中詳述許多黑人婦女覺得社工員傲慢無理——在這種基礎上建立治療關係簡直緣木求魚。
如果上述難題還不足以把個案工作徹底擊垮的話,到了1970年代初,許多社工員本身也開始反對或懷疑這種方法了。社會工作這一行早就知道,要保持社工員在「正確路線」(correct line)上極其困難。COS在二十世紀初開辦第一批正式社會工作課程,部份目的就是想灌輸一套他們希望是完整的知識,以免社工員被顯然漫長而瑣碎的個案工作法弄得氣餒。此外,他們和後來的社會工作領導人一樣,認為職業教育和訓練是限制進入此一行業的門檻,希望擋掉那些可能對貧困絕望採比較偏激或質疑立場的人。但面對窮人生活中物質匱乏的現實,要想保持理想主義的立場和作法談何容易,這些人很多集中在貧民區裡,悲慘和潦倒的情況觸目皆是,更強烈暗示貧窮問題可能是系統化的,而不是個人或家庭問題。
趨向管制和邊緣化
二十世紀趨近尾聲時,英國的社工員人數達到空前之多:1998年有53,900人。社會服務機構的規模和人員在地方政府編制內僅次於教育部門,而且和過去五十年一樣,仍以社會上最弱勢和最貧窮的人為工作重心。然而國家社會工作活動現在迥異以往,即使它的維多利亞時代先驅看到了,恐怕也辨識不出原貌。至少社會工作不再展現早年的信心和夢想,也不復西伯姆改革(Seebohm reforms)後那些年推動社會工作成長與擴張者的樂觀。現在幾乎沒有人再提個案工作重建社會上受損害最重者的生活的潛能,或它恢復案主成為良好公民的能力。它的公眾觀瞻和形象每下愈況,小報媒體似乎樂於宣揚它的失敗和錯誤。
社會工作早年的信心,大部份出於它自認為在解決根深蒂固的社會及家庭問題上特別有辦法,應該在社會福利系統居領導地位,引導及影響社會政策發展。這個夢想從未實現。相反的,社會工作在福利系統的角色日益吃重,但做的是別人撿剩(residual)的工作,保守黨或新工黨政府還維持社會工作,因為它在管理和監督社會最邊緣的人方面仍有價值。如果有些案主因社會工作而「獲救」(saved)當然很好,但社會工作的主要任務和控制、限量配給、監督,以及設法更進一步減少案主帶給社會福利的負擔,都屬於比較負面的工作。所以我們陷入矛盾:一方面社會工作機構繼續存在,而且規模大於以往,另方面它的工作從來不曾如此邊緣化和備受批評。
社會工作和社會排斥
有些人或許認為,這是保守黨在二十世紀後二十五年掌權將近二十年的後遺症,以保守黨長期砲轟國家福利措施,詆毀所有包括社工員、教師、護士和醫生在內任職公家機構的專業人員,這樣的結果沒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Hay, 1996)。然而,即使1997年工黨勝選上台,表面上揚棄新右派的下層階級觀點中比較冷酷無情的部份,用看起來比較人道主義的社會排斥概念取而代之,社會工作還是無法恢復昔日光環。
受到歐盟發展的影響,新工黨擁抱社會排斥概念,似乎許諾社會工作一個更美好的未來。這種概念關心包括絕大多數社會工作案主在內的社會邊緣人,從比較同情的角度看待貧窮問題和福利措施,不像以前社會工作受下層階級論點左右,用悲觀和譴責的態度評估最貧窮的人(Levitas, 1998)。此外,新概念附和社會工作長久以來的觀點,認為貧窮主要不是金錢(救濟金或工資等)匱乏的問題。反之,社會排斥牽涉多方面的剝奪,暗示案主受到排斥是一套加工過程(包括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製作出來的。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說過,「這是非常現代的問題,而且是一個比物質貧乏對個人傷害更大,更摧殘自尊,更侵蝕整個社會,更可能代代相傳的問題」(Blair, 1997, p.4)。
新工黨政府發動了不計其數的攻勢去打擊社會排斥,卻很少讓社會工作直接參與。部份原因可能是對抗社會排斥的策略和政策目光狹隘,只注意就業年齡有能力工作的人。如Lyons(2000年)指出的,新工黨非常強調支薪工作,視之為脫離社會排斥的途徑,反映在各式各樣的新政(New Deal)方案上,包括一項針對單親家長的方案。對目前許多社會工作案主而言,支薪工作機會既不相干也不適當。他們的問題可能是年老或患病,或純粹因為缺少可依靠的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而難以管理混亂的生活,這正是很多社會工作案主的生活寫照。看來新工黨在擁抱社會排斥概念之際,並沒有賦予社會工作服務一個新角色,反而是確定社會工作的剩餘地位(residual status),任由它在資源短缺的情形下,設法管理那些較明顯被歸類為失敗者和廢物的人。
那麼,社會工作和社會服務機構還能為貧窮和窮人做些什麼?從社會排斥議題的角度來看,答案似乎無關緊要,但談到如何管理和控制最貧困和最受傷害的人,這又變成非答不可的問題。社會工作不受重用,未能成為對抗社會排斥的積極策略,但它卻被賦予重責大任去管理、負擔和監督那些受貧窮傷害最深的人,還有那些被認為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無價值或不再有貢獻的老弱貧病。
社會工作實務
我對北英格蘭公職社工員的研究(Jones, 2001),證實上述頗為悲觀的分析並非無的放矢。我所作的訪談明白顯示,國家社會工作的特性已經改變,以往對案主困境的關懷和支持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比較官僚和管制的態度。我訪問的對象是在地方政府從事法定社會工作,多數具有經驗的第一線實務工作者,我從他們口中聽到的社會工作服務,千篇一律是士氣低落、壓力大、資源不足而受到嚴密管制(和查核)。不管從事哪方面的專門工作,這些社工員異口同聲的指出,由於獲得社會工作援助的資格標準改變,他們服務的對象通常困苦和貧窮。除此以外,就像我們懷疑的,經過三十年的福利縮減,以及英國國家福利制度新加的管束程序,社工員談到案主不抱希望而也無力取得足夠資源和服務來改善情況時,語氣都很絕望。可是,如這些社工員指出的,只要提高救濟金和養老金額度,就可以大幅改善大部份案主的生活。但新工黨的計劃已排除這個可能性,如Peter Mandelson所說的:「讓我們搞清楚這一點。那些我們關心的人,那些已到了窮途末路,瀕臨和社會脫節的人,不會因為每個禮拜多拿一鎊救濟金,就解決了他們的長期問題。」(Mandelson, 1997, p.7)。
我訪談的社工員沒有一人提到他們的案主需要個案工作,或表示案主陷入困境是因為某種根深蒂固的心理機能障礙。他們認為貧窮和隨之而來的困境是社會經濟趨勢和施政優先順序造成的結果。此處可以看出社會工作教育最近一些重要思潮對實務工作者的影響,尤其反種族歧視和女性主義觀點的貢獻;然而諷刺的是,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盛行和加強工作規範之後,社工員遵行反壓迫價值觀的空間,反而被壓縮得更小。這一點多少反映在實務工作者的卑微願望上,他們只想減輕案主的困苦,盡量增加一些福利救濟和服務。然而在一個已經變得約束、規定和控制重重的福利系統中,即使這樣的目標也難以實現。他們的機構讓這些任務很難達成,雖然有些人憑自己的經驗和技巧,還是有辦法比沒經驗的同事多爭取到一些資源。縱然如此,我還是聽了一籮筐的故事,包括官僚制度的層層關卡,填不完的表格和報告,開不完的經理匯報,說盡好話這些人才肯釋出一點點微不足道的資源。很明顯的,很多管制手段其實互相重疊,重點都是想要管理有限的預算和(and)控制社工員的活動。
這些故事從頭到尾給人的感覺是,國家社會工作的首要任務並不涉及任何有意義的復建(rehabilitation)或積極支持,也不能看成新工黨政府的社會包容方案(social inclusion agenda)的一部份。甚至不能期望它在減輕貧窮問題上發生任何作用。以家庭為單元的預防工作幾乎付諸闕如。與1989年兒童法(Children Act)的期待剛好相反,只有在孩子被列入「高風險」(at risk)名冊之後(after)——亦即只有在證明孩子遭到嚴重疏忽或虐待時,家庭才能得到援助。甚至到了這個地步,相關援助措施仍受到高度限制,通常很難取得,而在很多案例中,也不足以滿足家庭的需求。雖然我不輕視有些援助的價值,但傳統社會工作強調防患未然的重要性,現行援助方式顯然違背了傳統理念。此外,這些故事印證了Frances Rickford(1994)對兒童保護工作的批評,他說社工員「把時間耗在監督極度貧困者的親職習慣,但這些人需要的是實際援助,而不是監視」。一位最近退休的社工員補充說,「社工員都知道,這些父母只要能夠得到和比較幸運的家庭一樣的資源,他們對孩子的威脅自然就會消失」(Searing, 1999/2000, p.17)。
針對老年人和貧病者的法定社會工作也如出一轍。社會服務機構的社區照顧預算完全不敷案主需求,因此只有情況最嚴重的人才可能得到幫助。社工員為了讓案主取得居家照顧和療養資格,必須經過繁瑣的審查程序和沒完沒了的評估和報告。大多數機構不准社工員直接把案子送到分配資源的委員會,只能透過經理轉交,而哪些案子可以提交委員會,掌握預算的經理其實早有定見。聽社工員講述實際案例令人十分難過,有時候只要稍加干預,撥出一點點資源,就可以顯著改善一位老人家的生活,但因為他們病得不夠重,所以連這一點幫忙也得不到。
無力感是造成社工員精神壓力的主要因素(此一說法亦見諸Balloch et al., 1999, p.68)。他們對中上管理階層的反感令情緒更加惡劣,幾乎是異口同聲的咒罵;在實務工作者眼中,管理階層滿腦子都是政府規定的預算控制和新的稽核與績效指標,他們說新工黨在這方面比保守黨還要糟糕。結果是,社會服務機構在很多地方變得像工廠一樣。經理最重視的是單位時間產量和客戶周轉率(turnover):接受轉介,進行評估,然後盡可能迅速結案,而每一個步驟都須經過種類繁多的報告和表格確認,而且必須按照嚴格的時間表完成。雖然不能提出具體數字,但我相信很多案主在評估這一關就被刷掉,而且很多是在相當短的時間內被評估數次。難怪最近在利物浦進行的一項研究計劃(Anderson, 1999)顯示,住在該城一個非常貧窮地區的人認為,社會服務部門對他們在貧困中掙扎求生毫無益處。他們覺得社會服務部門是一個(除了評估)什麼都不會給你的地方。
結論
站在二十一世紀的開端,我們很難對英國的國家社會工作感到樂觀。在一個高度兩極化的社會,社會工作的功能和目的已經明顯改變,早期領導人的抱負在納入新濟貧法(new Poor Law)之後也已變質。新濟貧法一如它的前身,並不關心復健或社會包容(不管這個概念本身有多大缺陷),它所在意的是如何分配和控制給予社會上一些最窮困者的資源:這些人隱藏在社會一角,一般大眾根本不知道他們的悲慘處境。同樣默默無聞的是社工員的活動。很多公職社工員有很深的挫折感和不受重視的感覺,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多人想離職和這麼少人願意加入這一行的原因(反映在1995年到1999年間申請社會工作訓練的人員下降55%的現象上:Guardian, 2 February, 2000, p.8)。
對最貧窮的人來說,社會工作仍是非常不可信任的活動,而現在甚至比過去還無濟於他們在貧窮中的掙扎。
附錄:
窮人的感受
1996年法國慈善組織第四世界青年運動(ATD Fourth World)公佈一份報告,是關於英國的社會工作及其對長期生活貧困者的影響。該報告對英國社會工作沒有好評,並指出1989年的兒童法(Children Act)雖已載入夥伴關係的理想,但只是具文而已。窮人對社會工作的感慨,導致很多家庭在需要援助時,不會去找社會工作幫忙。這篇報告引述案主的心聲如下:
瑪麗‧涂坦姆帶著三個孫子靠每周一百英鎊救濟過活。「我們在樂施會(Oxfam: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的舊衣店買衣服。錢勉強夠糊口。渡假則免談」。她對社工員沒什麼好感。「他們派來一個年輕女孩,一點經驗都沒有,最喜歡說『我知道你的感覺』。他們何不問問我怎麼感覺。……專業社工員有他們的專業和友誼界線,不能夠越界。這個我了解,不過當你碰到危機時,他們總是看不好的一面。而你可能已經努力了三年不讓危機爆發。」
瑪莉亞‧瓊斯是兩個孩子的單親媽媽,她說:「我們只希望社工員把我們當人看。他們有時候到你家來,告訴你你家太亂。他們大部份都讓人討厭。」
摘自Community Care, 13-19 June 1996, p.l10。
五個要點
· 貧窮絕對還是社會工作形形色色案主最普遍面臨的問題。
· 不問專科和其他分科,社會工作這個行業最關心的絕對是人個中最貧窮階層的生活和行為。
· 社會工作理論和實務蘊含的個人主義和家庭主義(familialism),已使這個行業沒有立場去批判英國社會長久存在的不平等和系統化繁殖貧窮。
· 今天很多公職社工員都了解貧窮破壞和侵蝕其服務對象生活的本質,但他們缺乏必要的權力、組織和影響力去改變政府政策。
· 在最近政府打擊社會排斥的政策中,社會工作並未扮演任何重要角色。
三個問題
· 為什麼社工員面對窮人時,對自己的角色和責任如此不安?
· 慈善組織協會所持「不值得救濟的窮人」的概念,與新右派在1990年代大肆鼓吹的「下層階級」概念有無任何差別?
· 如果對當前社會存在的貧窮和平等採取比較批判的社會觀點,社會工作實務會有何不同?
延伸閱讀
· Becker, S. and Silburn, R. (1990) The New Poor Clients. London: Community Care。
· Wilkinson, R. (1996) Unhealthy Societies. London: Routledge。
· Jones, C. and Novak, T. (1999) Poverty, Welfare and the Disciplinary State. London: Routledge。
原載Martin Davies編《社會工作概論》,台灣群學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