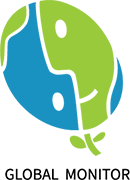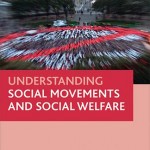
2010年 1月 6日
社會福利與社會運動之間的相互作用:社會政策探源
社會運動與社會福利,SPA論壇,2009年7月
作者:Gerry Mooney——公開大學(The Open University), Jason Annetts, Alex Law and Wallace McNeish——亞伯丁大學(University of Abertay Dundee)
社會政策協會年度論壇:“以史為鑒?”(Learning from the Past?)
2009年6月29日-7月1日,愛丁堡
張光明 譯
歐陽達初 校訂
【摘要】
當今時代的社會政策正面臨有史以來最為嚴峻的挑戰。從單純只要求住房、社會救助和反對關閉醫院的活動,到各種圍繞殘疾人權益、環境保護、醫療衛生和教育等方面的有組織運動,社會運動在全球範圍內正積極地挑戰和塑造著各國的社會政策。但是我們對社會運動在塑造社會福利政策方面的歷史作用一直缺少明確認識,而我們以往對社會運動的研究也沒有過多關照社會改革的歷史進程。
本文認為社會政策可以從社會運動理論中汲取變革的靈光,它只有通過瞭解社會運動的主張以及當今社會政策的內部矛盾,才能夠理解社會運動的緣起。我們通過綜合兩種「傳統」的觀點與方法,可以更好地去認識社會政策是如何受社會運動影響而被塑造的。
本文通過選取過去和當代的幾個案例,批判地考察了社會福利與社會運動之間的相互關係。歷史地看,社會運動直接導致了福利國家的產生(以貝弗里奇報告提出反對五大怪物——懶惰、無知、疾病、髒亂以及欲求──為標誌),但「傳統的福利國家」(classical welfare state)目前正受到「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s)的挑戰,這些新的社會運動主題涉及到家庭、歧視、環境保護和全球的社會正義。最後我們通過近期的幾個社會運動鬥爭案例,瞭解一下社會福利運動反對新自由主義階級統治危機的多種可能性。
一、上層推動的社會福利進程?(Social Welfare from Above?)
按照社會演化論(the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的觀點看,正如理想的民主就是19世紀所宣傳的「人人生而平等」那樣(當然後來才把女性包含進來),福利國家可能就是自由民主社會的最後發展階段,是文明自發進步的必然結局。馬歇爾(T.H. Marshall)那篇頗有影響力的文章《公民權與社會階級》(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1950年)就發表於戰後人們對英國福利國家建設預期最好的時候。他認為國家主導的平等公民權的建設(state-led equalities of citizenship),可以有效減少由於市場競爭導致的社會不平等。「這條被設計好的長路,通向更加充分的平等,通向不斷提高的社會地位」。在福利國家發展的「黃金時期」,通過授予公民權的方式實踐著的社會民主平等原則,其發展勢頭大有蓋過此前一直佔主導的不平等自由競爭原則。馬歇爾用輝格派的社會民主眼光講述了以福利國家為代表的社會演化論的勝利:「我認為社會平等的現代推動力,就是250年來連續不斷演化的公民權。」(Marshall, 1950: 7)按照這種觀點,英國是一個沒有單一核心的多元化社會的典型,各個利益集團之間通過談判和妥協構建起了國家的福利根基:「國家福利的發展相當穩定地維護了物質與權力分配。」(Thane, 1982: 300)英國長期以來保持了獨一無二的穩定與共識的傳統,這一點可謂是「非常顯著」。這兩大傳統如今也在國家福利的很多方面得到了體現。Derek Fraser (1972: 226)在他的歷史書《英國福利國家的進程》(The Evolution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中寫道:
「社會政策的制定必須要考慮社會組織對社會整體實際需求的反映,而福利國家的進程也是隨之一步步地推進的。福利國家並不是幾個世紀以來社會鬥爭的最終勝利,它只是社會政策在特定階段為適應下一階段的發展需要而對自身進行調整的一步步的過程。」
另有一些人從社會行政的「傳統」看,認為福利國家的進程也不是一條筆直的路線,反而帶有一些「浪漫的」曲折: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多種需求往往糾纏在一起。
「至少截至目前,福利國家的發展歷程總體上是不斷進步的,社會政策不斷地根據社會問題作出反應,也出現過意想不到的曲折,既有過對各種壓力的反應,也有過對部分人群的漠視,這一過程充滿了妥協和政治事件,也有機緣的巧合。總而言之,發生一切的可能都有。但不容置疑的是,人民的福祉不斷地得到提高,國家的力量不斷地得到強大,以及公民權利的日漸平等,這就必然會產生社會的福利體系。」(Bruce, 1968: 332)
但是演化論的觀點經不起時間的檢驗。近來對馬歇爾「公民權」一詞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它沒有考慮到當代英國的一些社會常識。因為馬歇爾及其同類人都或多或少想當然地把英國當成一個在種族和民族方面完全單一的社會,他們視野中的所有英國人都是白人、男性、基督徒。但英國社會最基本的分類是社會階級(儘管大家通常理解為職業的不同)。現在的英國已經是一個多元文明的國家,各民族的認同感也紛紛增強了(當然也有認同感稀釋和分裂的現象),女性參與社會公共領域的範圍也大為擴展了(Parekh, 2000; Lister, 1997)。這使得很多新的基於集體認同的權利要求也被紛紛提出,如民族權利、種族權利、宗教權利和文化權利等等。這一系列公民權利的提出就伴隨著一系列的新社會運動。
今天的社會運動所提出的公民權利遠遠超出了馬歇爾的狹窄視野,不再只限於以前政府為緩和階級衝突而給予的一些政治社會權利。不過當前這一系列新的權利要求,幾乎很少使用階級的語言。它們有過去早已存在的運動,如女權運動和同性戀解放運動,它們要求進一步擴大權利範圍或者要求變為性解放運動(Richardson, 2000)。還有一些新出現的環保運動或綠色運動,警告人類要關注情況危急的生態災難,並要求建立本國的和跨國的機構來關注生態問題(Cahill, 2002)。還有一些社會運動是圍繞著動物權利的(Regan, 2004)。可能所有這些運動都普遍蘊含著人們對人權本質的追求(Turner, 1993)。
儘管一些社會運動認為它們的訴求是「後公民身份」(post-citizenship)的、「後民族性的」(post-national),但這些眾多的權利訴求事實上都是以獨特的方式反映了當代社會發展的多元化。畢竟任何權利訴求都需要相應的體制化機構來支撐和保護自己的權利。馬歇爾把權利需求和國家機器分為對應的三個方面:法院代表著公民權利(civil rights),議會代表著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福利國家代表著社會權利(social right)。不過現在就很難清晰地把新的多元權利訴求和某一國家機器相對應了。1948年的《聯合國人權宣言》經常被當作經典引用,但正如Parekh (2000: 134)認為的,其中一些方案就不具備跨文化的適用性,因為它主要是建立在自由價值和單一國家的模式之上。這種文化相對主義傾向於認為新的利益訴求來自於價值理念而不是利益的差異,是「後物質主義的」(post-materialist)。在20世紀70年代初,馬歇爾自己也開始重估福利資本主義與新社會運動的價值理念之間的關係(Marshall, 1972)。這種「後物質主義」認為新的利益訴求完全建立在自身的價值理念之上,而與社會現實中的階級利益無關。它們的代言人有可能會成為代表某一特殊價值取向和特殊群體需求的封閉團體,而很少會觸及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與資產階級的民族國家。從社會學的角度看,當前關於新的多元價值需求的討論,迫使社會學必須要跳出演化論式的多元主義價值理念,而要更多更充分地去考察集體行為對福利國家的創立、發展與改革起到什麼作用?
二、下層推動的社會福利進程?(Social Welfare from Below?)
社會改革並不是憑空產生的,它至少需要這些歷史條件:客觀體制結構造成了束縛,但又有改變的可能;一場社會危機(如戰爭或社會動盪)造成歷史既有連續又有斷裂;觀念、價值的轉變;廣大民眾具有自下而上進行組織動員的意願。與高高在上的社會行政學派(馬歇爾為代表)不同的是,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想在眾多關於福利國家的論辯中,擺正一下天平,描述一下底層民眾的作用。當前很多關於社會運動作用的分析,都抹掉了下層人民的鬥爭對一些社會政策出臺的歷史貢獻。用湯普森(E.P.Thompson)的說法就是「後人太謙虛了。」。
這些下層民眾的鬥爭中,有一些我們是可以把它當做廣泛的「社會福利運動」,不過這也有好多種形式。在服務提供過程中的集體對抗行為就是一種社會福利運動。對於Harrison和Reeve(2002: 757)來講,這個詞的意思就是指:「一連串的有意識的集體行動及其相互作用:它針對勞資領域以外,關於社會服務的消費或控制,以及其是否能滿足個人、家庭或群體的需要與期望。」。在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是在衝擊福利制度,調整國家的政治結構。社會福利運動的特徵就是下層群眾的活躍分子與福利國家制度之間進行持久的、有組織的對抗。儘管我們對醫療、教育、住房、社會護理和社會保障等方面進行了眾多的具體研究,但我們卻很少在整體層面關注社會福利、政府機構與社會運動之間的總體關係。不過我們倒可以看出一個粗線條的過程:社會運動首先是通過言論或者受眾群體(user groups)進行直接的抗議行動,然後開始和政府的有關機構進行合作;在合作過程中存在著我們要維護自己的信念、而官方機構則要試圖對我們同化的政治衝突。這一點在現在越來越明顯了。
社會運動在1942-48年對英國福利國家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當然此前效果也很突出)。社會運動和勞工運動結成了鬆散的聯盟,共同爭取進步的教育改革、免費的現代醫療體系、公平的社會保障與權利分配體制以及要求加大住房建設等。這一熱情主要是英國人民延續了戰爭期間的政治熱情,以及1945年工黨贏得了大選的勝利。今天的福利國家仍然是當時社會改革的產物,它也是政治辯論和妥協的重要領域。同樣地福利國家仍然沒能完全擺脫意識形態的爭論,關於其本質的討論仍是「辯論的核心」。尤其是在20世紀60年代戰後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那時也是新「社會福利運動」出現的時候。
就英國而言,新「社會福利運動」抨擊了戰後以來形成的所有社會、政治共識,並積極要求和「舊的」社會運動討論如何對待新生的社會因素以及它們提出的新問題。新社會福利運動主要關注的領域就是福利體系,它們敢於抨擊了各級政府(地方、區域以及國家的)對有關集體消費福利(如公共住房、醫療、教育、交通等等)的措施,也攻擊官僚機構對福利體系的等級化僵硬管理。同樣地,它們還根據新的問題(環境、性別、性愛、種族和殘疾人等等)對早已被體制化了的「福利」的概念定義,進行了批判和修訂。
「新福利運動」包含了許多表達集體要求的團體,從愛滋病(HIV+)協會到生育權組織(reproductive rights groups)等等,它們之所以能聯合為一個統一的社會運動,是因為它們都以受眾為中心(user-centred),關注人們的基本利益需求和代表權,確保社會服務的供應和質量(Martin, 2001: 374; Williams, 1992)。當然它們也不同於其前輩。它們是在已經建立好的福利國家體系內開展活動的,它們的主要任務是保護現有的社會服務,並進一步擴大、深化和提高現有的社會福利,同時要堅決抵制任何部門刪減社會福利、設定一些排他措施。它們逐漸形成了一種「挑戰文化」(culture of challenge),經常質疑專家們的權威。現在新自由主義日益影響政府的社會政策制定,而這些運動組織已經動員起來捍衛社會福利的基本原則,捍衛與這些原則相關的機構與職位。
儘管20世紀60年代的人們政治熱情很短暫,但它對自由民主的政治理論與政治實踐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理論方面,它催生了無政府主義、政治生態學和革命社會主義,還將一些個人、文化和道德問題(如性別、性愛和家庭角色問題)政治化了。在實踐方面,它導致了很多非體制化的、非傳統的政治行為的大發展(如請願、聯合抵制、野貓式罷工、示威等等),並將這些政治參與的模式給標準化了。新的社會運動也在挑戰政府進行民主決策的傳統工具(政黨、公共機構)和過程。到21世紀初,社會的文化氛圍越來越體現出後六十年代的「行動政治」模式(doing politics):環保運動、人權運動、公平貿易和反資本主義運動,以及反戰運動(反對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還有無數的反對市場侵蝕公共福利的活動,此起彼伏!
社會運動也在日益進行跨國聯合與國際聯合,因為它們鬥爭的問題(環境公正、人權問題或經濟剝削)不可能在一個國家內解決,而必須進行國際的合作。全球資本主義的副作用也要求社會運動有一套全球的設計方案。Klein (2001: 84)認為:
「全球的社會激進分子都在跨國公司構建的平台上忙碌著。這也就意味著不僅跨國界的聯合,而且跨行業的組織都是必要的,包括工人、環保人士、消費者,甚至囚犯都與跨國公司有關聯。」
跨國的社會運動網路(經常得益於資訊技術和國際非政府組織(NGO)的支援)把社會運動的活躍分子們聯接成了一個鬆散變動的利益集體,他們共用著一些資源(資訊、組織、人員、經費等),共同對抗著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Klein說這是「為了人類的社會福利」。它們在1999年的西雅圖首次公開地聯合行動了。從某種意義上講,企業的研究機構及其右翼智囊團、主流政黨、學術機構、企業董事會、銀行、交易所以及媒體等等可能已經組織成了一個占主導的「來自上層的社會運動」,而廣大的社會運動組織,為了爭取建設一個以社會福利為中心的全球化,則組成了一個「來自下層的福利運動」。兩大運動相互鬥爭。
三、瞭解社會福利運動:理論與實踐的挑戰
社會福利運動已經在讓人們如何理解社會福利、如何利用社會福利方面做出了直接與間接的顯著貢獻,它們還在就很多具體的社會政策進行討論和發表自己的言論。它們所進行的所有活動都必然地與政府在各個層次發生衝突:地方的、區域的、國家的乃至跨國的和全球的層次。當然在有些時候,有些運動的領導人寧願成為國家政策的合作者而不是作為反對者。同樣的事情包括戰後社團主義階段的工黨領導人,後來圍繞性愛、性別和種族等方面要求「平等機會」(Equal Opportunities)的社會運動,以及一些融入到城市運動的鬥爭。
社會福利運動的另一特徵就是它們經常質疑專家的權威。這也經常被視為新社會運動的獨特特徵。只不過許多早期的社會運動是質疑權威專家是否足夠專業和誠實。失業者運動(Campaigns of the unemployed)經常討論什麼才是真正充分的社會保障,如何在制度上重新進行資源的分配。精英教育專家(Elite educationalist)過去備受批判,現在人們需求的是的綜合教育(comprehensive schooling)。這就是勞工運動的巨大作用。新社會運動的另一特點就是經常組織眾多的專家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提出另一番見解。它們最近就組織自己的專家反駁那些科學專家的言論,呼籲人們關注手機信號的輻射危害。當然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了,比如在醫療衛生領域,正是由於20世紀三十年代一些激進醫學組織如社會主義醫學協會(the Socialist Medical Association)和反營養不良委員會(the Committee Against Malnutrition)的不懈努力,英國政府才建立起國民健康保險制度(NHS)。當時的醫學專家們用自己的知識和地位呼籲實行社會主義醫療制度,減輕工人階級的痛苦。反營養不良委員會在30年代多次組織了大型公開會議,社會主義醫學協會則在工黨內部作為一個壓力組織發揮影響作用,它們的觀念為NHS的創立提供了意識形態和法律的依據。社會主義醫學協會在1981年更名為社會主義健康協會(Socialist Health Association),這也暗示著它將關注重點轉向了更為社會化的健康與福祉(well-being)。
社會福利運動最重要的政治意義就是它們改變了我們此前已經熟悉的舊的制度安排。改革被啟動了,職業實踐被改變了,官僚程式被簡化了,新的社會價值被廣泛認同了,關閉為區設施計畫被終止了,社會資源被重新公平分配了。人們的命運也從以前的消極被動、順從屈服和對社會政策的感恩,轉變為積極、自信、敢於發表言論。人們在政治、機構和職業中的命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福利運動對福利國家的建設起了積極推進的作用。這樣一種沒有限度(open-ended)的社會運動方式也意味著,當經濟蕭條時,它帶有的激進文化因數就會像過去那樣產生重大的社會運動浪潮,如1915年格拉斯哥的以及後來在克萊德賽德(Clydeside) 20年代爆發的更大規模的拒付租金運動(rent strike mobilisation),1935年南威爾士爆發的失業工人運動和1999年在西雅圖、2001年在日內瓦、2005年在愛丁堡發生的反資本主義運動。
難道真如Piven and Coward’s (1979)所說的那樣,窮人的運動只有是自發的、創新的、沒有組織的、有切實具體目標的,才能夠取得改革的成功嗎?但歷史的研究表明,他們的這種官僚式認識幾乎沒有任何史實的支撐。如20世紀30年代的全國失業勞工運動(NUWM (National Unemployed Workers Movement))就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運動組織,它有內部討論會、規定、捐款制度、報紙和帶薪的官員。它還組織了反饑餓遊行、在公路上睡覺(pavement sleep-ins)、佔領建築物、進行街道戰鬥。而在20年代初NUWM只是一個激進分子自發領導的地區性組織。當然NUWM的集中化也不是全面的,還有一些事務它要照顧地方支部的積極主動性(Flanagan, 1991: 167; Croucher, 1987: 104)。畢竟失業工人都是為了具體的物質利益而被迫採取集體行動的,他們是不會為了等候中央的指示而增加自己的痛苦了。
某種意義上講失業工人鬥爭的案例恰恰支持了社會運動中的「資源動員理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ies RMT)。首先NUWM提供了具體的物質利益激勵機制,失業工人有參與集體行動的積極性。他們追求更好生活的鬥爭,很顯然就是「填飽肚子的政治」(a politics of the belly)。對於失業工人來說,只要是能夠保衛或提高自己的利益,他們什麼都可以做。第二,雖說失業工人好像缺乏物質資源,尤其是缺少資金,但事實上他們的活躍分子——運動的主辦人(movement entrepreneurs)通常擁有巨大的組織資源,他們很多就是有經驗的社會主義者、失業的工會組織者和卸任的工會主管(ex-shop stewards)。最關鍵的是他們還有左翼團體提供的外部支援,包括組織上和意識形態方面,這使得失業工人的運動根本就不具備自發性。而且這種情況廣泛存在于各種的勞工運動、反種族主義運動以及健康、教育與住房改革的運動中。
然而從另一方面講,「資源動員理論」並沒有完全捕捉到福利鬥爭的核心內涵。雖然這些鬥爭都是為了直接的物質利益,但人們在鬥爭的過程中會超越具體的利益需求。這些鬥爭從來就不是純粹的戰略安排,它們每一個對社會公平的要求都包含有一個倫理尺度,包含一個觀念(新的生活方式)的鬥爭。Matt Perry (2007: 5)說:
「失業工人首先是為了追求認同而鬥爭,他們要求政府提供更充分的援助,是為了要求得到尊重和理解。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所承受的苦難,並不是由於自己的原因而產生的。」
而且「資源動員理論」也只是把研究局限在鬥爭的周圍環境,局限在具體的利益需求之上,它觀看的並不是一幅完整的圖像。它過早地把對鬥爭的分析限定在一定的層次上——最直接的需求,而沒有把這些鬥爭活動納入到更廣泛的、曲折的改革進程之中進行分析。
實際上某一運動的影響往往有一個時間上的滯後性,到那時一系列的社會環境都已發生變遷。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鬥爭運動就很好地塑造了戰後歐美各國的政治遠景,這是絕無僅有的現象。而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民權運動鬥爭則大大擴展了人們對普世民權的理解,原來還有那麼多的女性、殘疾人以及在民族、種族和宗教上的少數群體都沒有享受到過平等的民權。至今仍有很多組織向聯合國提議將1968年定為「民權年」。同樣,我們今天也仍在繼續感受到1999年西雅圖反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的影響,它揭示了資本主義在配置全球社會經濟資源方面存在的嚴重困境。社會福利運動一直在為福利制度的改革而時刻準備著,不過它們的價值理念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20世紀40年代,它們的價值理念是基於爭取普世的社會政治權利,而不是依賴隨意性的慈善行為;到了80年代就轉變為,爭取具有不同文化價值理念的群體都能享有平等的權利,反對歧視。它們對社會正義的種種要求實際上都是在衝擊市場自由分配原則這一曾經被視為不可褻瀆的神聖原則。可以說,縱然社會福利的受眾大部分在政治上不是很積極,但他們也確實不是「搭便車」(free riders),讓少數的活躍分子要承擔所有的風險而只坐享其成。
四、被解放的抗爭?(Protest Unbound?)
有那麼一些評論員(以及一大幫學者)現在開始大為貶低21世紀的失業工人運動或勞工運動,認為即使出現大規模的失業、社會動亂或福利銳減的情況,也不會有太大的反抗了(cf Bagguley, 1991)。他們認為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機構重組和官僚體制的更加集中化,已經把民眾大規模發洩不滿、進行大規模組織以及鬥爭文化的現實空間幾乎都給封閉死了。決策者和具體個人之間的遙遠距離使得民眾進行自我組織的再也不會像70年代那麼容易了,更無法與30年代相比了(Bagguley, 1999)。The Claimants and Unemployed Workers Unions在70年代強調了自己的自治地位、會員參與機制和反對任何被迫接受低工資的立場(Jordan, 1999)。新社會運動的另一特徵就是有意無意地仿效30年代的NUWM,但它們的激進文化可能也被誇大了。許多Claimants Unions會員整天忙於日常的演講和生活環境調查,根本就沒有了早期社會運動的那份激情。但即使是針對傳統市場原則的激進文化的意識形態和組織空間在過去三十年都被抹殺了。Bill Jordan (1999: 217) 說:
「公眾的抵抗運動其實很容易被鎮壓下去的,礦工們失敗了,印刷工人失敗了,但為什麼即便是沒有工會或政黨參與進來,失業工人們仍然相信他們能夠成功呢?其實他們並不指望由於自己的有組織行為而使得福利國家的體制有所改變。他們能夠通過自己的方式解決自己的困境,如去非正規的單位就業,進行策略性離婚、乞討、輕度犯罪、街頭賣藝等等。」
這些日常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被Jordan, and Piven and Cloward一類的學院派人士當作弱者對抗政府市場化政策的手段。他們歪曲了「底層階級」(underclass)的言語,把社會的問題顛倒為個人的問題,不道德地刻意去規定窮人的反抗形式。Hardt and Negri’s (2004)則進一步將其上升為「諸眾的觀念」(idea of the multitude),認為群眾不再通過集體的行為,直接挑戰政府的權威,轉而通過低水平的、類似於遊牧的遊擊戰進行匿名的遊行,畢竟眾多遊民的遊行能滋生混亂,會在很多方面影響帝國的根基。這種奇怪至極而又含糊不清的「諸眾」一詞,確實還曾短暫影響了一部分西雅圖集會人員。按照這種思路,直接的行動可以鼓勵不確定的自願捐助,發揚英勇的事蹟,光大理論與實踐相互作用的政治過程。
在21世紀前十年裡,這種言論的邏輯大行其道,一方面由於去階級化的新的社會運動的興起,另一方面由於新自由主義國家的市場主導政治,反倒為集體主義政治留下了空白。我們通常提到的「階級」一詞已經日益遠離其本身應有的政治學意義。自從20世紀60年代末起,由於社會的流動性增強、社會服務部門的人員大增以及勞動跨國分工的深化,工人階級已經被重新構建了,並且也日益顯得碎化了。政府為了應對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經濟危機,也越來越按照市場的原則逐步削減社會福利了。而此時新社會運動闖了進來,開始用一些「跨階級」(trans-class)、或「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t)的辭彙,提出了認同、文化、感覺、價值、道德等問題。它們站在政府與舊的社會運動之間起到了緩衝的作用,但又作為壓力團體、院外組織、有組織的政策論壇而保持了自身的獨立。
為了反擊這些對社會改革與社會動員的狹隘理解,我們從歷史中汲取的經驗就是必須要重新復活本真的社會運動。我們通過具體的組織活動,可以在那些人們不願意繼續以前的生活的地方,打開抵抗運動的局面。我們的運動要給人們以驚訝和奇跡。即使是運動的條件很差,它也能夠發生,因為這是時代發展不可避免的結果。即使是在20世紀30年代,也由於各國的環境不同,社會運動呈現了不同的發展狀態。比如在德國自從納粹上台後,社會運動基本上就被消滅了。而在法國,1936年的激進化反抗導致了法國持久的社會保障體系改革進程,即使是像現在薩爾科奇右翼政府也不敢阻擋。
當時,相比於美國實施新政的良好政治氛圍,英國的失業工人運動則面臨著國家政治環境的敵對。NUWM甚至都被媒體和官方的勞工組織罵為魔鬼,只是因為它在把失業工人組織起來。它的活躍分子勇敢地承擔了無數的個人風險,包括囚禁、員警暴力、經濟損失乃至犧牲。在那個年代,幾百萬人利益的爭取,靠的不是善良的政客,而是失業工人中少數活躍分子的直接行動。英國政治環境的敵對性顯示出,它應該建立起一套「政治機會機制」(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以便提前應對大規模的集體行動。面對著廣泛的政治敵對,這些少數活躍分子的英勇和果敢終於重塑了我們身邊的政治環境。
「後物質主義」的新社會運動,忽視了階級社會的複雜結構,強調了Bourdieu稱的中產階級文化至上的觀念,並將其提煉成是為具體的利益而戰鬥的理念。
可以說後物質主義只是進行階級劃分的技術標籤,它並不能準確反映出「階級」已經不再作為進行政治鬥爭的核心。或許由於世界經濟危機,全球資本主義的緊縮,各國政府對帶有戰略性目的的社會運動(「利益動員理論」指向的社會運動)降低了高傲的姿態。
在具體的實踐中,進行直接抵抗行動的各種組織、「運動企業者」(movement entrepreneurs)、很多社會主義團體和工人階級團體,它們之間經常會進行一些鬆散的聯盟。如20世紀90年代的反道路抵抗運動(anti-roads protests)以及最近的反對破壞環境建設(機場、購物中心、廢物焚燒爐等)運動,都出現過類似的聯盟。同樣地,近些年的反種族主義鬥爭,包括Anti-Nazi League、Rock Against Racism在內,還有很多工人階級團體的參與。西雅圖反全球化運動運動和「全球社會正義運動」(global social justice movement)給了我們一個清楚的暗示,針對具體的事情,一場充分而富有成效的聯合是可以發生在勞工運動人士和環保人士之間,卡車司機和海龜(Teamsters and Turtles)也可以進行聯合。而在法國過去十年裡,各種社會力量也針對國家的福利改革進行了卓有影響的聯合鬥爭。
總之,尤其在起碼的物質利益需求占主導的貧困問題上,人們反抗政府權力和專家意見的鬥爭方式是可以採取正式的社會運動這一傳統方式的。就像「平等機會」組織(the Equal Opportunities apparatus)那樣就是一個反貧困的組織,它的成員包括媒體人士、職業白領、政府官員和職員等。另有一些制度外的壓力團體如兒童貧困救助會(the 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它們的工作就是要告訴人們社會的貧困化和剝削水平已經達到了不可接受的程度,並著力影響政府政策的制定。在醫療健康方面,社會運動組織模糊地分為受眾者的組織和志願服務者的組織。還有一些像Benefit Rights Workers和國民建議中心(Citizen Advice Centres)的仲介組織,通過一定的規則和程式為窮人提供建議並為其代言,這樣就可以使困難群眾就不再是單獨作戰了,而有關人民權利的制度變革往往都是由於有組織的集體行為而產生的。
五、結論:夠了(Ya Basta)——通向社會福利運動的新政?
由於2008年的金融危機蔓延全球,一些評論家就哀歎社會運動沒有拿出一套解決方案。難道任何有壓力團體存在的地方,它們就能迫使政府和銀行改正其錯誤措施嗎?社會運動的廣泛努力(反失業、反貧困、反醫療、教育與住房改革等)是否已經針對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福利改革提出了另一套方案呢?過去幾十年裡勞工運動作為一個中間體確實對社會改革的推進發揮了巨大的歷史作用,它們通過長期艱難的鬥爭已經建立起福利國家的根基,並使人們形成了這樣一個共識:政府、勞工和資本三方必須要始終採取合作的態度(Harris, 1972)。
在更早期的經濟危機,如30年代大蕭條時期,各階級就和政府進行了緊密的團結。現在的一些評論家都認為那很「奇異」,但這確實是歷史給予我們的經驗教訓。
「興旺發達的20年代經濟到了1929年瞬間崩潰,這是企業和消費者負債累累的第一個黑暗時代,而我們剛過去的十年是第二個黑暗時代。在那些日子裏。人們甚至把自己的積蓄藏到咖啡桶裏,然後挖坑兒埋到花園裏。而英格蘭東北部的工人們則浩浩蕩蕩向倫敦進軍,當時被稱作加羅十字軍(Jarrow Crusade)。」 (Parker, 2008: 75)
另外一對例子是2008年10月的政府對金融資本(如銀行)進行一輪注資的救市行動(recapitalization)和20世紀三十年代的美國新政。在這兩個事例中,以前被奉為經典的自由市場原則都被拋棄了。而且同樣地,失業人數比例也都很高。到1933年美國約有1/4到1/3的工人失業(Galbraith, 1961) 。佛蘭克林•羅斯福上台後出臺了一系列的新政改革方案,有效地穩定了經濟,並減輕了窮人和失業者的痛苦。新政提供了眾多的就業機會,人們可以從中獲得收入並拿來消費,從而刺激經濟的復蘇。對於政治家和資本家而言,這種情況要比產生暴亂乃至革命好多了。事實也是如此,廣泛的社會動員和反解雇的靜坐罷工也對新政的出臺起到了有效的督促作用。在一些新政執行不力的地方,失望的人們便不顧一切地進行自救。後來全美國都建立了失業工人理事會(Unemployed Councils)。1932年一個作家這樣描述失業工人的激進行動:
「如果一個失業工人由於他沒錢而被停水停氣,他會去找相應的機構;但如果他窮的沒有衣服和鞋穿,他就會不顧任何壓力,也不再有膚色、種族和信仰的偏見,……他們會直接聚集在救濟所外要吃要穿,如果他們由於參加遊行、集會被捕了,政府還必須要給他們提供法律庇護。」 (Quoted in Zinn, 2001: 394)
美國新政的例子在當代也有迴響。如自1995年阿根廷遭受金融風暴以來,失業工人進行反抗的集體行動一直呈上升態勢(Garay, 2007)。這些運動隨時隨地都在為新政或貝弗里奇式福利國家改革準備著條件。不過這仍在進行中,還需進行更多的實際研究,並重新思考社會運動、社會動員和社會改革之間的內在關係。
今後關於福利國家未來建設的討論很可能會被公開提出來,因為各國政府也都在努力尋求應對新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方案。各國已經拿出幾十億英鎊的資金用於穩定國際銀行體系和刺激經濟復蘇。這些資金是在短期內從國際信貸市場借出來的,過一段時間這些錢還是要償還回去的。而英國可能會在2010年大選後提高稅收、削減公共支出。由於政府財政赤字非常龐大,公共支出很有可能會被大幅度削減。而隨著公共服務部門被壓縮,各種社會運動也會蓄勢待發。屆時英國現在的、還很不完善的福利體系還會剩下什麼呢?當然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要看社會福利運動的發展狀況:包括進行什麼方式的抵抗,參與力量有哪些,如何組織這些力量等等。還有這些運動能否變被動防禦為主動進攻?在不遠的將來削減公共支出已經是確定的了,這很可能會引起公共服務部門和政府之間的艱苦鬥爭,而這一鬥爭很可能具有決定性的政治意義,就像1984-5年間的煤礦工人大罷工那樣(Glover, 2009)。鬥爭一旦失敗,就意味著戰後幾十年發達國家福利制度終結的開始;而一旦成功,我們就可以根據21世紀的社會與環境需要,能夠更進一步重塑社會福利制度。因此現在的形勢非常嚴峻,社會福利運動組織要積極抵制任何對福利制度的攻擊,社會政策也應更多關注各種社會福利運動的利益訴求,而那些新出現的運動也要積極參與進來。
References
Bagguley, P. (1991) From Protest to Acquiescence? Political Movements of the Unemployed, London: Macmillan.
Barnes, C., Newman, J., and Sullivan, H. (2007) Power,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Renewal, Bristol: Policy Press.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ruce, M. (1968) The Coming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Batsford.
Cahill, M. (2002) The Environment and Social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Castells, M. (1977)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London: Edward Arnold.
Croucher, R. (1987) We Refuse to Starve in Silence: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Unemployed Workers’ Movement,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Flanagan, R. (1991) ‘Parish-Fed Bastards’: A History of the Politics of the Unemployed in Britain, 1884-1939,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Fraser, D. (1984) The Evolu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Macmillan.
Hardt, M. and Negri, A. (2004) Multitude, London: Hamish Hamilton.
Gabe, J. & Kelleher, D. & Williams, G. (eds) (2006) Challenging Medicine, London:
Routledge.
Galbraith, J.K. (1961) The Great Crash, 1929,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Garay, A. (2007) ‘Social Policy and collective action: Unemployed workers, community associations and protest in Argentina’, Politics & Society, 35.2: 301-2.
Glover, J. (2009) Caring Cuts are Just a Massage, Cameron will need a Hatchet, The Guardian, 23/03/09.
Harris, N. (1972) Competition and the Corporate Society: British Conservatives, the State and Industry, 1945-64, London: Metheun.
Harrison, M. & Reeve, K. (2002) Social Welfare Movemen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Lessons from Two UK Housing Studies, Housing Studies 17 (5) 755-771.
Inglehart, R. (1990)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lein, N. (2001) ‘Reclaiming the Commons’, New Left Review, 9: 81-89.
Law, A. (2008) ‘The elixir of social trust: Social capital and cultures of challenge in health movements’, in J. Brownlie, A. Greene and A. Howson, eds., Researching Trust and Health, New York and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Law, A. and McNeish, W. (2007) ‘Contesting the irrational actor model: A case study of mobile phone mast protest’, Sociology, 41.3: 439-56.
Lister, R. (2008) ‘Recognition and voice: the challenge for social justice’, in Craig, G., Burchardt, T. and Gordon, D. (eds) Social Justice and Public Policy: Seeking
Fairness in Diverse Societies, Bristol: Policy Press, pp.105-122.
Marshall, T. H. & Bottomore, T. (1992)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London: Pluto Press.
Marshall, T.H (1972) ‘Value problems of welfare-capitalism’,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1: 18-32.
Marshall, T.H. (1950)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in T.H. Marshall and T. Bottomore (1992)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London: Pluto Press.
Martin, G. (2001) ‘Social Movements, Welfare and Social Policy: a Critical Analysis’, Critical Social Policy 21: 361-383.
Norris, P. (2002) Democratic Phoenix,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rekh, P. (2000) Rethinking Multiculturalism: Cultural Diversity and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Regan, T. (2004)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arker, S. (2008) ‘Will it really be that bad?’, Sunday Herald, 26 October, pp. 74-5.
Perry, M. (2007) Prisoners of Want: The Experience and Protest of the Unemployed in France, 1921-45, Aldershot: Ashgate.
Piven, F, F, & Cloward, R. A. (1979) Poor Peoples Movements: 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il, New York: Vintage Books.
Richardson, L. D. (2000) Theorising Sexual Rights, Critical Social Policy, 20 (1) 105- 135.
Saville, J. (1957-8) ‘The Welfare State: An Historical Approach’, The New Reasoner, 3: 5-25.
Stewart, J. (1999) The Battle for Health: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edical Association, 1930-51, Aldershot: Ashgate.
Tarrow, S. (1994), Power in Movement –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ane, P. (1982) The Founda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Longman.
Thompson, E.P. (1970)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Pelican.
Tomlinson, S. (2005) Education in a Post-Welfare Society Lond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B, S. (1993) Citizenship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Williams, F. (1992)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Universality and Diversity in Social Policy’, in N. Manning & R. Page (eds) Social Policy Review 4: 200-19. Canterbury: Social Policy Association.
Zinn, H. (2001)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492-Present, New York: Perennial Class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