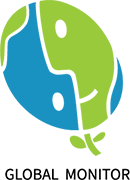1973年德裔英籍經濟學家舒馬赫(E.F. Schumacher)發表了他的名著《小即美》(Small is Beautiful)。舒馬赫批判資本主義那種盲目追求經濟增長和消費,公司規模,城市規模,無一不求其大,而結果卻是犧牲了人類福祉。他主張發展社區經濟和地方經濟,來抗衡後來稱之為全球化的那種盡量追求跨國投資和貿易的做法。在這方面他可說是其中一個先驅。
大即美
今天那種跨國投資與貿易所達到的程度,確實越加荒謬。你如果留意一下自己餐桌上的飯菜的來源地,就會知道,即使最便宜普通的食物都經歷千山萬水送來:菜心來自北京,牛肉來自巴西,雞蛋和大米來自泰國。但為甚麼新界就不能成為香港人的菜籃子呢?為甚麼不能在政府的扶持下,在那裏大力發展有機耕種呢?如是,則市民不受毒菜威脅,又省掉許多運費,減少許多溫室氣體,何樂而不為?
任何理性的社會都不應容忍這種荒謬的生產與消費制度。但是,你有你講小即美,官商階級繼續推行其大即美:公司越大越好,城市越大越好,連漢堡包也越來越大。所有產業,從銀行、電訊、保險,一直到醫藥、超級市場和連鎖快餐廳,都是越做越大,在關鍵行業更是達到幾十家甚至十家以內就壟斷了全球發達國家的主要市場。可憐的社區經濟,在這些跨國暴龍的壓榨下就越加前景黯淡。那些大得不能倒的英美銀行,如果在未來幾年縮小規模,那不是市場的無形之手的結果,而是國家有形之手的功勞。
大之外,還有快。市場競爭的壓力迫使資本家不斷進行通訊與運輸上的技術革命,去縮短距離,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稱之為時空壓縮。貨幣,商品與勞動力加快流通,讓資本的周轉加快,一筆資本可以當兩筆,三筆,四筆用。壞處是你追我趕迫使大家做事要快,講話要快,走路要快,吃飯要快。近年在歐洲開始有人發起減慢運動(go slow movement),不過,除非你不用工作,否則要慢真難。
有人把1970年代以來的資本主義稱為後現代,同舊時代大為不同了。但是,即使這個時期同過去有甚麼不同,資本主義還是同過去一樣繼續好大喜快,繼續違反理性的生產、消費與文化發展,繼續違反人類福祉。不管是現代還是後現代,資本邏輯繼續發揮作用。
資本的必然邏輯是甚麼?就是資本的積累。「積累啊!積累啊!這就是摩西和先知!」[1]。資本是一種價值,但不是一般的價值,而是能夠增值的價值。它不只增值一次,而是要不斷增值,不斷變大,這就是資本積累。資本絕對不能夠有知足常樂的想法,不能滿足於保值,因為在競爭的規律下,唯有增值,它才能保值。唯有進,它才能不退。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客觀強制性,不以資本家個人意志為轉移。只能純粹保值的資本,早晚要被競爭對手打垮,變成對手的財產(這就是資本的集中)。
資本和市場,兩者都歷史悠久,但它們並非任何時候都具有這種力量。這是因為,千百年來兩者都受著政治、宗教、倫理、地方勢力等等的嚴重限制,因此資本無法自由流動,市場的競爭也無法真正自由展開。只有到資本主義時代,競爭的規律才全面展開,資本積累才無限制地發展起來。
指出資本邏輯的必然性,不等於承認它是唯一的必然性,不等於說反抗是絕望的,更不等於否定人類有意志自由。恰恰相反,資本邏輯的必然性也必然激起被統治階級的反抗激情。這是我們理解150年來的世界史,理解今天圍繞城市發展的一切鬥爭的鎖鑰。
城市化與資本邏輯
資本的積累,在物質上既表現為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同時也表現為城市化,即「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樂和需求的集中」。[2]資本積累不僅決定經濟結構,從而是就業結構,它也決定著城市的生死。美國矽谷的繁榮和底特律的衰敗,本身就是美國資本積累策略自1970年代以來發生巨大改變的結果。香港的歷史本身也體現著資本積累過程的變化和地緣政治的衝突:1842-1949年,香港是帝國主義在中國大陸的轉口港,1950-1980年之間是孤懸大陸之外的反共基地和出口加工區,然後,在1980末至今則一方面回復大陸轉口港地位,另一方面又上升成為金融中心。但是這個雙重地位,正在因為大陸資本主義的騰飛而日漸受到威脅。當中國的歷史性崛起完成之日,就是香港又一次根本改變之時:能夠升級為中國的紐約的機會不高,而下降為中國的三流城市則不低。
雖然資本本身沒有恒久不變的形態,它可以是貨幣資本,商品資本,土地資本等等,但哈維的貢獻是他提醒大家,資本的積累本身,又必須以一定的空間為基礎,而這首先是城市。[3]在一個訪問中,哈維說:
「我們所居住的城市,本質上就是資本累積的過程。」
「忽略城市,只把國家當成唯一的實體,這是有問題的。當然,在聯合國投票的是國家,這個答案,大家都覺得有理,我也不例外。但是,從金融流動的角度看,紐約和倫敦之間所具有的緊密來往,程度上比美國和英國之間要高得多。」[4]
目前,城市人口已經占了全球一半;過去幾十年,超過一千萬人口的超級城市到處拔地而起。中國在這個競賽中更獨占鰲頭。同時,在這些超級城市中,貧富分化以特別醜惡的形式表現出來,一方面是高聳入雲的商業大廈和超豪別墅,另一方面則是嚴重污染的貧民窟。但是兩者都受同一個價格運動的支配。不斷從農村和各地流入大城市的貧民,移民和商人,使城市土地價格總是趨於上漲。地產商可以從豪宅中謀利,也可以從窮人中謀利。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這個早期著作中,就談到1840年代的倫敦:
「地價隨著工業的發展而上漲,而地價越是漲得高,(資本家)就越是瘋狂地在每一小塊土地上亂蓋起房子來,一點也不考慮居民的健康和方便,唯一的念頭就是盡可能多賺錢,反正無論多壞的小屋,總會找到租不起好房子的窮人的。」[5]
21世紀的香港「屏風樓」現象,不過是同一個資本主義城市化的基本法則的作用而已。
資本主義城市化最為不公義的其中一點,就是:城市每一幢大樓都是建築工人蓋起來,他們也是工業意外的最大受害者,但是他們,如同一般工人一樣,卻總是居住在貧民窟和窄小的工人住宅區。勞者不獲,獲者不勞,在城市住宅上面尤其突出!不只這樣,連這些只夠供棲身的住宅,其下面的土地只要升值,立刻就會有地產商密謀趕走他們。恩格斯晚年著作《論住宅問題》,再次回到城市化與住宅這個題目,並特別指出,這種土地價格的運動正是造成工人住宅總是短缺的原因之一。
城市化意味官商階級必然掠奪土地:一方面是對舊城區土地的掠奪,另一方面是對城郊土地的掠奪。這是全世界都經歷過,而且還在經歷的過程;20年來,這個過程在中國上演得尤其徹底而又醜惡。一直到1970年代末,香港這個過程其實也是又徹底又醜惡。從前舊區或者新界哪個地方,政府發展計劃,不論是建鐵路/道路,還是發展新市鎮,多數意味剝奪當地居民的土地。同時,由於地方勢力(特別是新界地主),往往與官員勾結,首先得悉發展計劃,及時收購土地,所以成為這些發展計劃的最大得益者。打從1980年以後,過程基本沒變,迫遷的新聞簡直不是新聞,只是官商勾結從此做得更為隱蔽而已。
再把歷史眼界放得久遠一點,城市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發展,歷史前提就是剝奪農民土地,迫使他們流入城市去當資本家的雇傭勞動者(英國16世紀所謂羊吃人就是最典型例子)。中國則是另一種剝奪方式:鄉鎮及村官通過稅費把農村搞到破產,迫使一億五千萬農民出外打工。
時空壓縮:運輸與通訊
城市的物質生產,市場的交換與商品的消費,在在需要發達的運輸系統和通訊系統。哈維在《不均地理發展理論筆記》一文中寫道:
「(資產階級)有很強烈的個人和集體動機,要將資本的周轉時間降到最低,而且,我們因此看到了,有許多創新是為了加速生產、行銷和消費。既然距離是以移動的時間和成本來衡量的,就有強大的壓力要藉由運輸和通訊創新,來減少距離障礙。商品、人員(勞動力)、貨幣和資訊移動的成本與時間,馬克思所謂的『經由時間消滅空間』而減少,這正是資本積累的基本法則。」
「必須有空間上固定且不能移動的運輸及通訊系統等實質基礎設施(港口、機場、運輸系統),才能將其他資本和勞動形式解放出來,達致更便利的空間移動。運輸投資會被吸引到主要生產、金融和商業中心,因為這裏是最有利可圖的所在。」[6]
換言之,利潤率決定了資本主義的城市發展必然錦上添花,而不會是雪中送炭:越發達的城市地段(西九),吸引越多投資;反之亦然(天水圍)。而運輸系統則確保這種人、財、物的流向符合資本的需要。這樣就形成一種循環,對資本家來說是良性循環,對勞動者來說是惡性循環:越繁盛的地方,地價越貴,越吸引資本投資於交通運輸(又或者游說政府去做冤大頭),而交通越發達本身又再推高地價。高鐵要放在這樣一種歷史框架中去理解。
城市的魅力
資本積累促進城市化,城市化又反過來加快資本積累,成為資本家呼風喚雨的力量。但是,資本積累又不得不同時創造出自己的最可怕的敵人 --- 現代無產階級。1848年的歐洲工人革命震動了統治者。城市把這些可能成為資產階級的掘墓人的現代無產階級集中起來,對於統治者實在是一個重大威脅。法國的拿破侖第三在革命失敗後想出一個對付辦法:找來建築師歐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把小街小巷的巴黎統統推倒,改建為大街大路,使巴黎工人不能再那麼容易築起街壘搞起義了;而四通八達的大道,又方便了政府派出軍隊鎮壓。1871年梯也爾果然花了不大功夫就鎮壓了巴黎公社,這要多得歐斯曼。(隨便一提,歐斯曼以至許多官商,都因為巨大的巴黎改建計劃而發了橫財,而恩格斯也不忘在《論住宅問題》為歐斯曼算這個賬。大工程必有大貪污)。不過,1968年法國革命證明,歐斯曼的成功始終是暫時的。
當代發達地區的城市,其社群關係和階級關係當然比較十九世紀複雜得多。但這只是一面;另一方面,它也是蠻簡單的。複雜在於,受城市不公義發展影響的社群,不再是單一的「無產階級」,而是包括大批所謂「中產階級」,也包括許多小業主、租客、貧窮社區、關心飯碗的工人、環保份子、保育分子、學生等等。但是,另一方面,由於資本積聚和集中的規律,推動不公義城市發展的元兇卻越來越單一:就是壟斷資本及其政府。[7]所以抗爭主體雖然是多元的,但抗爭對象卻是一樣。這就是反抗不公義城市發展的階級性的一面(當然還有其他方面)。
城市化把資本集中起來,成為資本家賺錢堡壘。但是經濟功能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城市化同時也把各個中下階級和社會群體集中起來,把各種反抗運動集中起來,把來自五湖四海的人,連同他們各自的文化,藝術與歷史,都集中起來。這種集中常常激蕩出新的文化和藝術潮流。這在古代城市已經是這樣,到了資本主義時代更加厲害而已。同時,這種文化繁盛的創造者,不限於知識階級。在1840年代,在英法兩國到處可見的那一代的工人活動家,通常不是雅各賓主義者就是共產主義者(也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志;《共產黨宣言》就是受他們委托而寫的),往往從自學中成為作家和藝術家。「他們建有工會圖書館、技工講習所、圖書館和科學俱樂部,也設立畫廊、傳教集會、戒酒聯盟、嬰兒學校,甚至還創辦花藝協會和文學雜誌。」[8]對他們來說,為飯碗而鬥爭,與為精神生活而鬥爭同樣重要。拿破侖第三和歐斯曼所摧毀的舊巴黎,同時也摧毀了工人社區的精神文化和人情紐帶,並因此而為工人所唾罵。總之,城市文化的不斷變遷,本身部分來源於資本積累的後果,但有更多是其他領域的變化的結果。這些其他領域,包括城市各個社會集團之間的社會、政治的鬥爭,更包括各種思潮和風格等等精神文化領域激蕩的結果。我們不能說美國黑人的靈歌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香港50-70年代的電影混合著廣東文化和上海文化元素而帶來新的風格,本身也不能從經濟因素直接找到原因(或許除了一點:香港工業的發展,為電影提供了新一代的觀眾 -- 「工廠妹」)。城市把文化多元性集中起來,形成了一種驚人的創造力,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寶貴的精神力量。這就是城市的魅力。[9]文化發展,如同愛情一樣,越是不受經濟必要性(首先是生存的必要性)支配,就越可愛。
不過,要保護這種精神力量,恰恰需要認識資本主義的本質,而越是認識它,就越了解到,對人類文化發展的威脅,不多不少,正是來自資本。資本積累要不斷開拓新的商機,才能完成使命。當工業產品市場越加飽和時,它就必須轉往其他領域,而且必然找到:文化領域同樣商機無限。對它而言,整個世界,整個地球,全部文化,都是商機:the world is for sale! 資本積累越是周期性地陷入危機,它就越需要把萬物商品化。馬克思從資本主義表現為「龐大的商品的堆積」[10]來入手研究資本主義,這並不是偶然的。哈維寫道:
「資本主義將生活網絡中,許多不是生產為商品的基本元素,都當成了商品。這適用於勞動,適用於一切我們經常指稱為『自然』的東西,以及我們社會存在的特殊形式(最明顯是貨幣,但是也包含像文化、傳統、智慧、記憶,以及物種的物質再生產等特性)。一旦身體成為公然的『積累策略』,異化就隨之而來了。(例如在人類基因上賺錢 – 劉按)」[11]
「例如,考慮占用文化歷史來當成商品以供觀光消費的情形。資本對壟斷地租的追求,創造出某些現象商品化之後的酬賞,而這些現象在其他方面則是獨特、真實,因而是不可覆制的。掠奪文化歷史、收集和展示獨特物件(各種博物館),以及地方作為某種獨特環境的行銷,在近幾年裏成了一門大生意。」[12]
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認為城市化由於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為社會主義創造了物質前提,所以必然是善。他倆常常不忘指出,這種發展的不合理的地方,它怎麼違反人性,它迫使人和環境付出甚麼可怕代價,因此反抗它是多麼重要。城市化一方面帶來經濟、文化和藝術等種種活動的集中,但是這種熱鬧的另一面,就是城市人的孤獨。恩格斯在上面提到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寫道:
「像倫敦這樣的城市是這樣壯麗,簡直令人陶醉。…但是,為這一切付出了多大的代價,這只有在以後才看得清楚。難道這些群集在街頭的成千上萬的人,不應當尋求自己的幸福嗎?可是他們彼此從身旁匆匆地走過,好像他們之間沒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們彼此毫不相干,只在一點上建立了一種默契,就是行人必須在人行道上靠右邊走,以免阻礙迎面走過來的人;同時,誰也沒有想到要看誰一眼。…這種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難堪,愈是可恨。…這樣就自然會得出一個結論來:社會戰爭,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已經在這裡公開宣告開始。…結果強者把弱者踏在腳下,一小撮強者即資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窮人卻只能勉強活命。」[13]
當代那麼多偉大小說和劇本,寫的不是人類的幸福和快樂,而是他們的不幸、寂寞和異化,這本身也是一種不幸。這個文學現象再次提醒大家,一切聰明才智,一切最著名的文化藝術活動,都集中在城市,但不見得幸福與快樂也集中在多數城市人身上。這難道不應該叫人反省城市化嗎?所以,馬克思認為,社會變革需要把消除城鄉的對立,重新規劃人口和經濟活動,確保其集中程度符合人和自然的和諧相處,人和人的和諧相處。但這種變革,又需要以停止資本邏輯繼續支配社會為前提。
反資本主義聯盟
指出資本邏輯必然要壓縮原本屬於集體或個人的空間,把他們所擁有的東西商品化,不等於承認它絕對成功。恰恰相反。我們重覆一次:資本邏輯的必然性也必然激起被統治階級的反抗激情。我們當然可以選擇「將自己按照我們心中欲望來創造城市的個人權利,退讓給地產擁有者、地主開發商、金融資本家和國家」,但是也可以選擇反抗。圍繞城市發展而引起的鬥爭,由於涉及許多不同群體(小業主、租客、貧窮社區、關心飯碗的工人、環保份子),所以「並非所有這些鬥爭都是古典馬克思主義意義下的『階級鬥爭』」,而是具有多樣性(人們可以以不同理由去反高鐵:保家園,保育,環保,反貧富懸殊,反資本主義等等),既有保衛物質利益在內,也有追求精神財富在內(其實二者並不對立)。哈維告誡左翼朋友,如果左翼「忽略了當代條件下這種鬥爭的多面向特質,形同放棄打造反資本主義聯盟,而這種聯盟本來是能夠做一些事情,來遏止掠奪性資本主義的所作所為的。」[14]
當然不是每個參與者都想「反資本主義」。在實際鬥爭中左翼當然要尊重盟友的不同出發點。但是,另一方面,向盟友耐心解釋,這也是左翼的責任:為甚麼資本邏輯必然違反理性的生產與消費,必然破壞環境,必然把優雅文化商品化、從而庸俗化;而許多局部的反抗其實可以理解為全面反資本主義的其中一些步驟。從長遠奮鬥來說,反抗者只有認識資本邏輯,才能制其死穴,才能有效保衛並擴大社會文化的多樣性。只有認識必然性,才能找到自由。後現代主義諱言「資本主義」,認為那只是老左的「堂皇論述」;或者拒絕討論「資本的必然邏輯」,認為那是「本質主義」;總之,結論就是:因為當代社會還存在著許多不受資本邏輯支配的空間。只要我們找到它,它就能讓我們過另類生活,何須研究甚麼資本邏輯?更有人認為,應該研究「甚麼不是資本邏輯」才對。然而,事實是,資本的萬物商品化的邏輯,恰恰正在每日每時扼殺原本不受其支配的空間。哈維在他的《不均地理發展理論筆記》一文,有針對性地說:
「其他理論家假設了有受保護空間(福柯命名為『異質地方』)的存在,在裏頭,日常生活和情感關系的運作,可以不受到資本積累、市場關系和國家權力的支配。…我同情這個整體目標,但認為它錯誤且自毀長城地假設了某種異質地方或分隔之『生活世界』的存在,這種空間隔絕了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和概念。接受了『生活世界』和『系統』這樣的區分,會導致拋棄馬克思交到我們的,有關歷史唯物論探究原則的每件事情。畢竟,馬克思尋求的是日常生活的批判知識。他的方法導向『對於存在的一切事物的無情批評』。…我們就必須承認目前在工作場所,以及生產-消費過程中發生的每件事情,都以某種方式陷入了資本循環和積累。幾乎我們現在吃喝穿戴,收聽,觀看和學習的每件東西,都以商品形式來到我們面前,而且有分工、產品利潤的追求,以及體現資本主義信條的論述與意識形態的一般演化所塑造。」[15]
如果地產商已經把路修到最後一個桃花源,而你還說,那麼我們就搜尋桃花源中還有沒有小桃花源吧!這不是開玩笑嗎?不,我們應該挺身而出,同資本邏輯對抗,從反高鐵運動開始,一直到廢除資本邏輯的支配地位為止。是以全球正義運動叫出「世界不能割賣!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the world is not for sale,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的吶喊,它之所以激動人心,因為它對症下藥。哈維甚至在最近一篇文章中,請大家思考,是否需要提出一個新口號「另一個共產主義是可能的!」呢。[16]
話說回來,左翼應該體認到,從來沒有一種信念適合所有人,即使它自認其反資本主義信念以理性分析為基礎。莫說某些從根本上挑戰理性思維的後現代主義者,始終對馬克思主義(西方意義上,不是中國意義上)不服氣,就是堅持理性思維的,也有人(而且是更多人)出於各種信念而不服氣。人的思想和性格,本來就是多種多樣。即使同一個階級地位,也永遠存在各種思潮,誰也說服不了誰。那種認為工人階級只應有一種論述,或者「一個階級,一個黨」的思維,應該擯斥。左翼如果參與辯論,如果想駁倒對方,既為了把歧異弄清楚,也為了求同存異,但絕非妄想說服所有人。在社會抗爭上,定然是各路英雄分進合擊。
結語
反高鐵運動這種圍繞城市不公義發展的鬥爭,不止可以追溯到喜帖街和皇后碼頭的行動,還可以追溯到更遠一點,例如1978年元州仔木屋居民反遷拆事件,1979年上水安樂村居民反逼遷被鎮壓事件,還有同年的艇戶反逼遷等等。就像香港的民運歷史並非始於1986年民主促進會一樣,香港的反拆遷運動也並不是始於21世紀。再從橫切面看,今天菜園村,性質上其實同近年來中國大陸此起彼伏的反拆遷行動也是一樣的。發掘歷史和放眼全中國以至全世界,不是也不應是為了表示「古已有之,何足為奇」,「境外有之,你算個啥」;相反,而是為了增強今天青年反抗的道義力量:啊,原來吾道不孤!
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但願菜園村在香港進步青年的支持下,成為香港最牛釘子戶!
2010年2月7日
[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22章第三節,652頁。
[2] 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選集卷一,56頁。
[3]哈維談到空間對資本積累的重要性,也是為了說明,資本積累的地域性意味地緣政治始終重要,意味資本主義不可能廢除地域性競爭和國家霸權。又由於地理空間必然是不平衡的(例如資源的分布),所以資本的積累過程也必然是不平衡的。為重新瓜分資源、市場和有利的地理位置而鬥爭,就成為資本主義必不可少的內容。這種觀點正好同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 對立
[4]http://www.theory-talks.org/2008/10/theory-talk-20-david-harvey.html
[5] 馬恩全集第二卷,336頁。
[6] 載於《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王志宏翻譯,群學出版有限公司,臺北,2008,95-96頁。譯文略有修改。
[7]要指出,政府偏袒壟斷資本,這本身不會因普選而改變。不過這是後話。
[8] 《革命的年代》,艾瑞克·霍布斯邦,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臺北,311頁。
[9]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寫道:「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對馬克思來說,社會主義只能是由城市工人階級運動來領導,而不能夠是農民。
[10]資本論第一章第一段
[11]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王志宏翻譯,群學出版有限公司,臺北,109頁。
[12]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王志宏翻譯,群學出版有限公司,臺北,87頁。
[13]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arxist.org-chinese-engels-1845-3-15.htm
[14]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王志宏翻譯,群學出版有限公司,臺北,84及110頁。
[15]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王志宏翻譯,群學出版有限公司,臺北,76-7頁
[16]http://davidharvey.org/2009/12/organizing-for-the-anti-capitalist-trans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