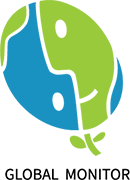2009年 3月 23日
過去主流的社會工作實務把受助者視為純粹救助對象,而且把他們的困境主要歸結為個人問題(例如個人性格缺憾、際遇、品德),與社會結構和社會政策沒有直接關係。不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出現多種多樣的學派和思潮(激進社會工作、女權主義社會工作,到80年代興起的反壓迫實務等),紛紛質疑這種把案主視為客體的傳統觀念,而開始強調案主的主體性,以及社會服務員和案主之間的平等關係;也開始批判傳統社會工作建基於個人主義的心理輔導取向的局限,而強調案主的個人困境很大程度上源於社會制度和政策等結構性原因。例如家庭暴力發生與受害家庭成員普遍社會經濟地位低下兩者密切相關。因此,同工在提供服務時,一方面需要引導案主認識造成其困境的社會根源,另一方面認識到案主不僅有權自決,而且他們其實是有自主性和主體性的。
受助者,您的名字是...
那麼,社福界同工的服務對象究竟是些什麼人?是的,他們具有不同或多重的身份:公屋居民、精神病患者、受重建影響的舊區租戶、失業者、綜援人士、少數族裔、家暴受害者、隱閉長者、隱閉青年或濫藥者等等。可是,除了各自不同的身份外,他們大多數還有一個身份是大家共同擁有的:他們絕大部份來自下層,是並不富裕的階層。確切地說,他們其實是廣義的勞動階級(普羅大眾)的組成部份。勞動階級是指那些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階級,他們並不擁有或控制著生產資料,其收入也不足以累積資本,只有依靠出賣勞動力(包括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來維持生活的群體。據此,勞動階級不僅包括傳統產業工人(例如工廠女工、建築工人),還包括一般僱員(護士、教師、社工、售貨員、推銷員等),更包括那些「處於社會邊緣」而「被社會遺忘和遺棄」的弱勢群體 1。
指出這一點,好像沒什麼稀奇,但是不要忘記,過去一段時間,社福界的服務零碎化,令我們忘記了社會服務其實一直埋首於貧窮和社會排斥問題。在社福界裡的服務使用者,或稱「用家」,絕大多數是窮人,來自人口結構中最弱勢的階層。社會服務與其他行業不同,它具有很強的階級特殊性(class specific)2。就像人需要呼吸空氣的事實,因為習以為常反而不被察覺一樣,社會福利致力於改善普羅大眾的處境,好像大家覺得習以為常,反而被漸漸遺忘了。
大多數受助者擁有共同的勞動階級身份──指出這點,其實是有意義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階級佔大口中的多數,而資產階級佔人口的少數,兩者的利益是根本對立的。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中,工資和利潤之比處於不斷鬥爭之中:上層階級往往取得大份,而下層階級取得小份。在經濟繁榮時期,由於勞動者的生活還算過得去,表面上好像「勞資雙贏」;但是當經濟危機來臨時,兩大階級的利益對立就清晰可見了。所以,只要不把眼光局限於各自獨特的身份,而上升到整體財富分配的層面,就不難看出,勞動階級是處於相同的社會地位、具有共同利益的,他們往往需要協同抗爭,而不是滿足於各個特殊界別的單打獨鬥,才能抵抗上層階級的壓迫。而且,勞動階級並非永遠是「弱勢社群」,其實他們還是「強勢社群」,只要他們認識到其生活處境如何被政治經濟的因素決定,以及被「去福利化的社會政策」(diswelfare social policy)影響,並敢於發聲及反抗,由「被去權」變為「被充權」,他們就能夠從自在的階級(class in itself)轉變成強有力的自為的階級(class for itself)。
公民權倒退
很多研究社會福利發展的學者 3 都指出:社會福利的多寡(是否普遍獲得、非商品化的程度)與階級力量對比,兩者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在十九世紀初資本主義工業化開始時,根本沒有什麼社會福利,後來是隨著勞動階級的團結鬥爭,才開始迫使資產階級提供一定程度的福利,例如勞工保險、公共房屋、全民醫療等等。
社會政策學者馬歇爾(TH Marshall)歸納公民權利可分為三大類:民權(個人自由、私有產權等)、政治權(普選權)和社會權(全民就業、接受教育、退休保障等)。過去200年,西方公民權利的概念已從民權擴大到政治權以至社會權。1945-1970,是戰後福利國家的黃金時代,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工黨、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等改良主義政黨的執政造成社會權的擴展。過去,香港公立醫療體系聲譽不壞,其實也是仿傚英國國民保健服務(NHS)的結果,而NHS是工黨戰後執政開始推行的其中一個重要福利措施。
我們沿用馬歇爾的說法,可以把最近30年全世界普遍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理解為公民權利的倒放膠卷現象:從社會權退到政治權,再退回民權(如強調個人財產權)。問題是,為什麼出現這樣急劇的倒退?關鍵在於階級力量對比起了變化。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把新自由主義視為「階級力量的復辟」4 ,意思是指1980年代開始隨著資產階級新右派代表(列根、戴卓爾)上台,勞動階級的力量節節敗退,再加上蘇聯東歐集團的崩解和中國回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導致福利國家的備受攻擊和社會工作的蛻化(社區工作的萎縮、社會工作公義價值的蛻化),讓資本主義的邏輯(利潤最大化、成本考量、競爭、市場化)普遍化。這一切,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新自由主義所代表的階級力量──資產階級實行反攻倒算,要把福利國家時代勞動階級一度多少享有的社會權利收回。哈維進而認為,新自由主義改惡給我們的教訓之一是:「如果某種現象看起來像階級鬥爭,我們就必須名副其實地稱它為階級鬥爭」5。
「新公共管理」與福利改惡
在香港,作為一種理念的新自由主義(曾蔭權常用「小政府、大市場」來形容它)是通過1990年代末興起的「新公共管理」理論(New Public Management , NPM)作為中介,來達致社會福利的改惡。「新公共管理」認為最有效的行政和專業改革來自市場機制,它有兩大假設:第一,市場提供的服務必然比政府提供的更靈活,更低成本,也更有質素;第二,一切社會政策問題都可以用較好的管理技術和方法去解決,改善管理是所有問題成敗的核心,而外判和私營化是公共管理的最佳方法。
我們在一份社會福利署1999年出版的供資助機構推行「服務質素標準」(SQS)參考的實務手冊,可以讀到這樣的文字:機構優質管理的背景是「各政府大致上相信市場機制及商營管理手法的優越性:小政府理想」。為此,「福利機構面對政治、經濟、科技,及社會環境的壓力而需要作出適當的反應及改革」,包括「政府實施購買服務或外判服務;政府角色由服務提供者轉向協助者及購買者」以及「透過競爭性的投標機制選擇適合的服務提供者,而服務提供者可包括非牟利及牟利團體,以實現混合福利制度模式」。一個貌似正面的「服務質素標準」改革,其實也充滿著「新公共管理」的新自由主義和管理主義思維。往後的社福界改惡措施,例如整筆撥款、服務競投,莫不是沿著「新公共管理」的思路實行的 6。
新福利觀的元素
如果以上分析成立的話,所有希望打破目前的困局,不甘社福界就此沉淪下去的同工,恐怕需要在日常組織工作中更多強調「階級政治」:
* 具備階級視野,看到不同種類的受助者同屬一個階級,在社會政策影響下,他們有著相同的處境和命運;
* 具備批判的視野及反思的警覺,思考其「專業」身份與受助者的權力不均,及傳統的慈善、救濟及剩餘性的社會福利觀,是為受助者帶來更多的「充權」還是「去權」。
* 前線同工與案主其實也屬同一個階級,是大家共坐一條船的命運共同體,應該更強調雙方的平等關係,盡量消除監督和控制;
* 案主不僅是社會福利的受助者,還是可以產生主體意識的群眾;經過集體行動,他們能夠提升意識,分享集體經驗,開始反省和拋棄種種基於獨特身份而普遍存在的落後意識(大男人主義、性傾向歧視、看不起新移民...),並在尊重差異的基礎上重建階級意識和階級團結;
* 經濟危機下,社會服務員更需促進失業者和情緒困擾者通過集體行動自助自救,例如鼓勵促成各種各樣的自助組織,這比起「正向思維輔導」、霎時感動的「心靈雞湯」等愈來愈個人化的心理治療更具進步意義。我們需要重新發現社會工作的「集體取向」(collective approaches),更多反省傳統「個人──心理取向」的局限。
* 明白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的根本利益對立,明白統治階級為了實行福利改惡,不得不在下層中施行分化、拉攏、挑撥,而大眾往往只有整體視野(即階級視野)才能避免被分化,而把矛頭一致向外。反失業聯盟1999年初的反對削減綜援宣傳活動中,就提出過「綜援唔係高,人工低到無晒譜」、「削減綜援,誰人得益?」、「在業失業齊團結」等標語,意在抗衡統治階級分化在業者和失業綜援人士的技倆。2007年中紮鐵工潮開始不久,婦女、學生、長者等民間團體組成了「全港各界支援紮鐵工潮聯合陣線」,一連串的支援行動多少扭轉了罷工初期對紮鐵工人不利的輿論。當然,我們也經歷過失敗的例子,例如1999年房署員工反對公屋管理私營化時部份居民團體和民間團體冷淡甚至反對的態度。
* 建立新的福利觀,亦需要具備「階級政治」。以香港為例,1997年經濟危機之後特區政府的政策摧毀了不少自麥理浩時代開創的福利服務。最近的「金融風暴」,預料統治階級將再次轉嫁危機,把他們一手造成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惡果由下層人民來承受。福利的進一步收緊、公共服務進一步外判化、人口政策上的倒退、製造「依賴文化」論甚至挑動「窮人鬥窮人」,已經在統治階級的盤算之內。勞動階級的團結和意識強化,將有助打亂統治階級的如意算盤,有助保衛現有的社會權利和爭取更大的福利權。
身份政治還是階級政治?
1980-90年代一度盛行的後現代主義和身份政治,在肆意拆解主流意識形態(包括主流福利論述)方面,有一定的貢獻。她對特殊身份的強調,令我們更注意過去被輕視的一些社會關係及隱藏其中的權力運作,令同工和組織者保持敏感度。這都是後現代主義不可否認的價值。但是,後現代思潮那種對現代性的一概否定,對啟蒙價值(自由、平等、博愛)的拆解,對任何「宏觀論述」的質疑,令她流於相對主義,充滿犬儒性格。總之,後現代主義解構有餘而抗拒合理的建構,令她不能對福利權運動和其他民眾運動的發展提供真正有效的指導,反而淪為資本主義的化妝師。例如,過去對弱勢社群的明顯歧視去污名化了,「殘廢者」改稱「不能自助者」,「弱智人士」改稱「智障人士」,可是他們的實際處境和壓迫並無絲毫改變,這樣的去污名化最終不過是協助統治階級建構「政治正確的資本主義」。
放眼世界,自新自由主義肆虐近30年到處造成貧窮和不公,特別是10年前西雅圖爆發反世貿示威從而開啟全球正義運動(反全球化運動)之後,客觀形勢急需一種既能夠包容多元性又能整合力量的進步思潮和進步運動,即需要真正進步的「宏觀論述」,以抗衡「歷史的終結」、「除了市場經濟外,沒有別的選擇」(TINA)等統治階級的新自由主義「宏觀論述」。在這個新的形勢下,那種過份迷戀於微觀的論述解構又抗拒整體結構變革的後現代主義福利觀,就格外顯得不合時宜。
追求一個公義的社會
總括而言,階級視野和階級政治比較能夠理解社會政策的發展、理解新自由主義福利改惡的根源並指導爭取福利權的方向。1960-70年代,在歐美婦女運動、民權運動、工人運動、同性戀運動和學運等民眾運動蓬勃發展的背景下,催生出進步社會工作和實踐。後來,隨著1980-9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興起,進步社會福利觀一度沈寂。今天,一方面新自由主義造成的危機已然爆發,另一方面社會福利的市場化和管理主義改惡已經引起同工和服務使用者的焦慮、不滿和反抗,再加上反對市場霸權的全球正義運動已經出現,客觀環境應該比1960年代更有利(至少同樣有利)於催生一個新的進步福利運動和社會工作實踐,更廣泛連結同工和服務使用者,去追求一個公義的社會。
2009-3-21初稿
2009-3-25定稿
注釋:
1.當然,上層階級之中也有患精神病、家庭暴力等問題,但是,第一,出現嚴重個人困境的受助者多數屬於低下層;第二,富人有較充足的資源及社會網絡解決個人困難,但窮人面對的處境較艱難,他們較容易成為社會服務機構的服務對象;第三,社會工作的傳統核心價值就是幫助弱勢社群,而非無區別的惠受所有階級,這是她的基本使命。
2.Chris Jones〈貧窮與社會排斥〉,載Martin Davies編《社會工作概論》,台灣群學出版社,2005。
3.I Gough , Esping-Andessen等
4.〈新自由主義與階級力量的復辟〉,載哈維著《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台灣群學出版社,2008。
5.同上,頁60。
6.參見林致良〈社福界重災區是怎樣做成的?〉,載《超越「小政府、大市場」──批判新自由主義香港社運文集》,監察全球化聯陣出版,2006。
參考書目
1.Ian Ferguson, Michael Lavalette and Gerry Mooney《反思福利:批判的視角》(Rethinking Welfare: A Critical Perspective ), Sage , 2002
2.Iain Ferguson《奪回社會工作:挑戰新自由主義與促進社會公義》(Reclaiming Social Work: Challenging Neo-Liberalism and Promoting Social Justice) , Sage , 2008
3.〈「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社會工作與爭取社會公義的鬥爭〉載Iain Ferguson. , Michael Lavalette , Elizabeth Whitmore編《全球化、全球公義與社會工作》論文集(Globalisation, Global Justice and Social Work), Routledge , 2004
4.英國社會工作行動網絡〈社會工作與社會公義:呼籲新實踐的宣言〉,見http://www.socialworkfuture.org/?page_id=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