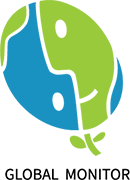Fiona Dove 與Daniel Chavez的對話
2015年10月09日
作者: Danie Chave
中文翻譯: 蘇菲亞
「民主能源(energy democracy)」的概念對我們應對氣候變化和能源貧困的挑戰有何貢獻呢?
攝影:K.H.Reichert /Flickr
世界各地許多社會、政治和環保份子都已經把「能源民主」的概念納入其語言、建議書和要求裡面。我們現在日益形成的一個共識是,為了阻止氣候變化,以及讓所有人都能公平獲得能源,我們必須進行體制上的變革、打破由跨國巨企對全球經濟的霸權控制,以及民主化公共部門。跨國研究所(Transnational Institute, TNI)的執行董事,Fiona Dove,與我們的一位研究員Daniel Chavez,進行對話,談論了能源民主方案對歐洲和全球南方的意義、影響和範圍。
什麼是「能源民主」?
在過去的五年中,能源民主的概念已被歐洲多個社運組織廣泛接受,他們特別關注到大型企業在能源的生產和分配方面日益佔據主導角色。
能源民主的定義現時已有幾條,但一般來說,它們的意思是重疊的,都表示一個權力較為分散及由公共社會控制的能源體系。在某些情況下,也有針對重奪國有企業的具體可能性;它亦指出了國有或地方公共企業的民主化,甚至指將之前私有化的電力公司歸還公眾手中,即「重新國有化(renationalisation)」或「重新公有化(remunicipalisation)」。
在許多地方,能源民主的概念也和當地的倡議或方案有著密切的關聯,例如利用可再生能源來生產及配電的小型合作社。
很多人都會認為地方的、及權力分散的體系才是「真正」的能源民主的形式,但你指的形式也包括了公共事業;而公共事業往往是較大型的、權力集中的,及非民主的。
沒錯,你說得對。公共事業並不總是最理想的。但在一些國家,人民已經可以通過國家的、區域的或地方性的、而且是國有的能源設備而廣泛獲得可靠的電力服務的時候,就沒有必要完全轉換到其他的離網選擇,或拆除本來就存在的設備。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的是公共部門的民主化,這意味著讓公民真正參與公共事業的營運方式,並確保窮困人士或其他弱勢群體也能得到適當的能源服務。在某些情況下,這是一個非常艱鉅的任務。
幾個星期前,我受到南非金屬業工會(NUMSA)的邀請,參加了一個關於現今南非面對的電力危機的會議。會上討論到的其中一個重要議題是,如何重掌國家電力公司——Eskom——這一大型企業的控制權。許多與會者都認為該公司已被嚴重公司化(即該企業仍是國有,但其運營方式如同跨國集團),要進行民主變革簡直是烏托邦、不切實際的;而最明智的選擇也許是創辦或重振市政或地方的公用事業部門。
但我不認為解體Eskom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案,因為它可以打開私有化的大門;再說,也不能保證之後的小型公用事業部門就會較為民主、高效或負責任。
能源民主的概念除了電力之外,是否也能應用在能源的其他領域?
沒錯,確實是這樣。現在不少的社運家和研究人員是來自碳氫化合物的領域的;但是,主要的觀點在於能源的自主權,因為他們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一直努力對抗那些開採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的外資私人跨國公司。我們在哥倫比亞、尼日利亞和加拿大多處不同的地方目睹了這種抗爭。
我們都同意,眼見地球氣候在快速變化,我們急需關閉化石燃料行業,但我們需要一個好的過渡計劃,讓那些石油和天然氣儲量豐富的國家繼續利用其現有資源一段時間,讓他們有足夠資金開發轉移到可再生資源。
歐洲那些在爭取能源民主的社運人士已採用這個論據,表明我們不可以讓跨國巨企私有化了屬於大家共同擁有的可再生資源,不可以讓之前開採北海石油和天然氣儲備的事件重蹈覆轍。
這樣的討論也活躍於那些仍依靠煤炭發電的地方,例如希臘。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在最近的撤銷方案之前,他們原本的競選綱領包括了轉型到可再生能源過渡期間的具體方案:逐步減少對褐煤的依賴,在二十年內實現一個較為環保的能源體系。
在能源領域裡,「重新公有化(remunicipalisation)」的意思是什麼?
「公有化(municipalisation)」或「重新公有化(remunicipalisation)」並不是一個新的趨勢。在跨國研究所的「水公義」項目中,我們一直有跟進著全球北方和南方多個重新公有化的事件,包括一些大城市如布宜諾斯艾利斯、巴黎、阿克拉和吉隆坡。在2000年至2015年期間,已有超過230個由地方政府重掌水務和衛生服務控制權的例子。
在能源領域,由市政及地區性的公共部門來負責供電服務已有數十年。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世界各地的許多城市把多種公共服務都納入市政範圍,大部份就是因為私人營運商只為富區居民提供水電,而忽略了窮困社區。
根據美國公共電力協會公佈的數字,今天,即使是在美國這資本主義制度最核心的地方,也有超過2,000個由市政及社區擁有的公用事業,為4,600萬市民提供服務。當中包括了洛杉磯、西雅圖和奧蘭多等大城市,以及全國各地多個小城鎮。不幸的是,並非所有的地方公司都是真正公共的、民主的,和環保、可持續發展的。
在歐洲,電力領域也正在出現重新公有化的發展趨勢。巴塞隆拿的新市長Ada Colau——她以前是西班牙反迫遷運動的領袖,曾帶領一支由多個激進政黨組成的聯盟,發起多次的運動—— 幾個星期之前宣布了政府將開始成立一個全新的地方性的公用事業,以解決該市約10%的、處於「能源貧窮(energy poverty)」困境的城市家庭。
歐洲另一個有趣的經驗是「柏林能源圓桌會議(Berliner Energietisch)」。這是一個由50多個社運及環保團體於2011年所建立的聯盟,以重奪德國首都供電服務的自主權為目的。它旨在推動成立一個新式的、建基於環境的可持續性發展、社會所有權及民主管理的市政公用事業。
該運動最後爭取到了2013年11月舉行的全民公投,其中有約60萬的市民投票贊成重新公有化。遺憾的是,儘管有80%的選民投了贊成票,但還是不夠票數,該次公投僅僅差21,000票就能達到法定投票率的要求。儘管如此,爭取成立公有的能源公司的公民運動仍在繼續,柏林能源圓桌會議仍在積極抗爭,同時也啟發、鼓舞了歐洲各地發起類似的倡議運動。
在歐洲以外,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更雄心勃勃的發展傾向——「重新共有化(republicisation)」。我用的這個詞是由Massimo Florio新造的;Florio先生是米蘭大學的一位研究員,他帶領的團隊正在收集、研究世界各地私有化營運的逆轉案例。在拉丁美洲,各處均有多而廣泛的重新國有化(renationalisation)的發展進程,特別是在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以能源領域來說,該發展過程始於2006年的玻利維亞,時任總統是左派的Evo Morales,宣布把天然氣工業國有化。隨後,於2010年和2012年他又先後分別把發電和電網營運也國有化了。在委內瑞拉,Hugo Chávez政府在2007年完成了供電服務的重新國有化。
總體而言,我們可以把這些結果視為正面的例子,但對於國有化的細節還是有很多值得討論的空間,例如國有化實施的方式、私人集團在轉移資產予國家而獲取的財政利益、國有化的範圍,以及國有化後的公共企業的內部管理問題等等。我們必須認識到,國家並不會總是高效率的,正如委內瑞拉的國家電力系統現時所暴露出來的毛病。
這些經驗說明了我們是可以把私有化逆轉過來的;而同時,在重新國有化之後,政府就要負起改善其服務質量的責任。幸運的是,我們在拉丁美洲也有其他的國有電力公司來證明,在適當的政治條件下,國有的能源公司也是可以很有效率的,例如烏拉圭的國家電力公司UTE,以及哥斯達黎加的國家電力電信公司ICE。
相比起其他區域,能源民主的概念似乎在歐洲比較普遍,真的是這樣的嗎?
歐洲的社運人士已廣泛接受及應用能源民主的概念,但在全球南方還不是很普及。在拉丁美洲或非洲,我們比較傾向於採用「能源主權」的概念,通常與糧食或土地等其他社會抗爭有關。但是,我們指的並不是不同的抗爭;「主權」的意思也隱藏了人們對基本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分配和消費的控制權,可以是糧食、飲用水或電力。它意味著更大的社會控制權,即從目前支配著全球經濟的企業和市場為主導的機構中重奪控制權。
而我們可以看到,在全球北方和南方,大家的抗爭其實都差不多。比如在希臘,能源民主的思想也深深根植於主權和自決的理念中,並強調希臘人有權在不受債權三巨頭協議規定的限制下,具有規劃和實施國家能源政策的權利。
在其他國家,例如烏拉圭,能源民主意味著逐漸轉型至非傳統之可再生能源,以減少對進口能源的依賴,以及受區域及能源市場波動的影響。
在墨西哥,現任的新自由主義政府實施的能源改革的內容就是為了抵禦石油和電力部門通過自由化而最終被私有化的結果,以確保墨西哥人民的需要,而非私營和跨國企業的利益。
你剛才提到烏拉圭和墨西哥,你能進一步解釋一下這兩個地方的經驗嗎?
墨西哥的能源部門經常被國際商業媒體形容為一個失敗的體制,只有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才拯救得了。《經濟學人》雜誌甚至寫了一篇關於墨西哥需要「一個全新的墨西哥革命」的報導。在過去的兩年中,該國已改寫憲法,並通過新的法律來結束國企Pemex八十年來在石油和天然氣生產方面的壟斷營運。電力領域也正在逐步開放,使另一家大國企,聯邦電力委員會(Federal Electricity Commission)的生存漸受威脅。
其假設是,改革將能更有效利用墨西哥尚未開發的潛在能源, 其中包括了大量的頁岩儲量,其儲量有可能比該國的北邊鄰居們,以及其主要貿易夥伴,美國,更多;同時也可以提供較為便宜的電力服務。
事實上,把墨西哥化石燃料資源的控制權轉讓到私營企業對墨西哥人民、以及我們的地球來說都將是個壞消息,因為該國的經濟和公共財政收入有很大部份取決於其能源領域。從全球南方眾多國家的實踐經驗證明了,向私營及跨國公司開放開採和服務領域的大門,往往為新的投資者帶來快速和客觀的收益,但卻為居民帶來永久而慘重的損失。
我的祖國,烏拉圭的情況則相反。目前向非傳統之可再生能源的轉型已經被多個國際媒體稱之為能源「革命」。跟南方其他國家不一樣的是,供電在烏拉圭並不是一個問題,因為早在數十年前,國家電網的覆蓋率就已達到99%以上。烏拉圭的問題在於其電力的來源。
烏拉圭經驗的國際相關性是舉足輕重的,因為我們談論的不是一個小島或一個只具備基礎經濟活動的小國家,而是一個比比荷盧經濟聯盟(Benelux)大一倍的國家,以及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高於波蘭、匈牙利、克羅地亞及許多其他歐洲國家的國家。同時,烏拉圭經驗另一個有趣之處在於,一家國企——烏拉圭國家電力公司(UTE),一家高效率的公共企業,在轉型過程中,針對風力發電進行快速、即時和巨大的投資,一直帶領著國家過渡到一個可持續的能源模式。
本屆政府(左翼陣線聯盟自2005年開始執政)的目標是在2017年年底前,把風力發電量從現時佔總電量的13%提升到37%。 這將使烏拉圭可媲美於全球風力能源的佼佼者——丹麥;該國43%的電量來自風力發電。
在豐水年,烏拉圭靠其三座水壩可以生產所需總電量的75%;但在乾旱的時候,國家被迫花很多錢在燃燒燃料上面。風力能源的發展增加了電力供應量,不僅使烏拉圭在電力消費方面可以做到自給自足,還有多餘的電力可以出口到鄰國的阿根廷和巴西。
順便說一句,我另外感到很自豪的一件事是,在烏拉圭的反對服務貿易協議(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TISA)運動,以及支持環保和勞工組織工作的運動中,跨國研究所也一直參與其中。我們最近剛剛慶祝了烏拉圭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個拒絕服務貿易協議的國家。該項協議以及其他類似的貿易和投資協定,例如環太平洋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或歐洲的「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TTIP)」一樣,會嚴重威脅到那些負責提供電力、水務、通訊等基本服務的公共企業的生存空間。
那在當前關於能源民主的辯論中,是怎樣考慮國家的角色的呢?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我已經多次提到國有企業、國家政府和市政府,但就沒有解釋國家機構在目前的辯論以及現實世界中能源民主鬥爭中的重要性。
我知道我們在歐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朋友和同盟對國家角色有很批判性的觀點,運用很多史上和當前的例子來說明那種由上而下、過度集中的能源服務提供模式既不民主,又沒有效率。有些批評亦指出現在很多國家實行廣泛的新自由主義,經營能源部門(包括了電力和石油天然氣的開發採購)的國有企業大力擴張,營運模式猶如私營的跨國企業。
對於這些批評,我大部份都贊同;但有些政治主張我則不是每次都認同。我不認為社區擁有的模式或可持續性能源的合作方式是國有企業以外,唯一可行的替代品;或者我們就要因此而放棄國有模式。正如跨國研究所另一位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Hilary Wainwright所出版的一本很好的書的書名所說,我們應該「重奪國家」。對於我們這些擁護馬克思傳統的朋友來說,大家都很熟悉「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這個理論;但最近在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發展趨勢告訴了我們,國家並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內部同質型的機構;國家是可以因應反霸權的社會及政治運動的壓力而進行改變的。
我覺得改革家們現在是時候要去克服一直存在於左翼份子之間的二元矛盾:一邊是那些著重自主自治的、自我組織的權利來源的支持者;一邊是那些仍然相信需要奪取及管理國家權力的社運份子。我們不能忽視最近在左翼政黨的推動下,世界各地有多個不同的政治實驗證明了,自主自治和基層權力之間可出現創新連接,以及國家轉型的可行性。我指的是那些豐富的、正不斷增長的、Erik Olin Wright稱之為「真正的烏托邦」的倡議運動。
Naomi Klein在她最新出版的書中提醒我們,阻止氣候變化的唯一途徑是要戰勝資本主義;氣候變化也是解決很多其他社會問題的一個機會。這並不意味著我們需要來一場像1917年俄國革命那樣轟轟烈烈的運動來擺脫資本主義。事實上,我相信突發或暴力的革命已不再可行。相反的,我們應該推動「非改革派之改革(non-reformist reforms)」,該改革模式可以有效地消除不公正或壓迫,包括發展反霸權的、又可替代國家來提供公共服務的另類選擇。但這也意味著要建立起足以抵消資本主義擴張的非資本主義機構。也就是說,地區性的可再生能源合作社,以及民主的、管理完善的公共事業都可以被視為「真正的烏托邦」。
過去三年我的研究重點在公共企業,但我並不會把國家的角色理想化。我很清楚,公共事業不應被理解為會內部自行進步的機構,也不應因為他們非私人擁有而一直袒護它們。我研究過哥倫比亞麥德林(Medellin)一家市政擁有的公司,EPM,它本是一家非常社會化、高效率及負責任的,為當地提供電力、水務和電信服務的機構。但近年來它開始進行國際化擴張,吞沒了哥倫比亞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各地的私有化公用事業。在哥倫比亞境內,它的表現猶如私營公司,安裝預付費水電錶,並切斷那些無力支付費用的用戶的服務。
EPM就是我們所說的「公司化(corporatisation)」的一個典型例子:國有的「公共」公司,但其營運方式無異於新自由主義的商業手法。但我自己關於國有企業的研究也顯示了,要改善和民主化公共部門是完全可以的,而公共擁有權也仍然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你認為在這些問題上,跨國研究所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呢?
正如我們研究所的名字所指,跨國研究所專注於跨國家的議題,能源問題無疑就是屬於這類型。前些日子,聯合國大會正式同意了一系列的新目標,稱之為「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其中一項就明確提到了可再生能源:SDG7。這也是一個持續的運動,其中包括了把2012年定為「人人享有可再生能源國際年」,以及潘基文「人人享有可再生能源(SE4ALL)」的倡議。
在跨國研究所,我們通常對於全球性倡議的前景和影響都抱著質疑的態度,這些倡議的特點是大量的浮誇言辭、毫無新意的論述,以及重視跨國企業利益而置社會需求為其次(SDGs已更名為「全球目標」,以使之在以企業為主導的宣傳活動中聽起來比較吸引人。)
但我們很歡迎的一件事是,所謂的「國際社會」已確定能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至少在對話層面上,似乎大家都同意我們要在2030年轉型到一個可持續性的能源環境,確保服務的全面普及、大大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並把全球改善能源效益的速度提高一倍。
而現今的社會運動、政治及環保運動的核心就已包含了該轉型所需之驅動、內容和具體特徵。然而,重視能源民主概念的我們所捍衛的思想,跟那些企圖在紐約遊說聯合國或在布魯塞爾說服歐盟的跨國巨企們亮麗堂皇的說辭所表示出來的想法是大大不一樣的。所以,我們覺得跨國研究所一定要組織參與國際運動,和世界各地其他組織一起合作,分享我們的關注和想法,以增加壓力促進一個更可持續性、更民主的轉型。
最後一個問題,你多次提到水運動;你覺得在能源領域中,我們可以發展出類似的運動嗎?
在供水服務方面,跨國研究所從事反對水務私有化及支持公共控制權的運動已超過十年,我覺得我們從它們的抗爭中可以學到大量經驗。最近在布魯塞爾由羅莎·盧森堡基金會(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舉辦的一次會議上,一些與會者就提到了,如果我們想建立能源領域方面的國際運動, 我們可以更仔細地研究、學習一下「水戰士」的模式。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世界各地有不少能源方面的抗爭運動,但並沒有類似於水運動的那種全球性的協調行動或共同平台的模式。我們同時也需要與其他組織建立起更密切的聯繫,例如「能源民主運動工會(Trade Unions for Energy Democracy initiative)」。
渥太華大學的教授Susan Spronk就寫了一篇簡短但非常有見地的、關於抗爭經驗分享的文章——「石油與水是可以混合的:能源與水資源的公民抗爭」。在文章中,她解釋了橫跨全球南北方的社會運動如何在反對水務私有化方面取得重大的勝利,並指出工會、學者和其他社會組織可以通過學習這些抗爭,建立起能源民主運動相關之地區性和國際性的聯盟。
我們知道,能源和水務的政治經濟體系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但我們可以借鑒水運動家們的經驗,學習如何構建我們的要求,與盟友合作的重要性(儘管有時我們不完全認同大家的政治觀點),以及如何加強我們自己的組織的內部民主。
英文原文:
https://www.tni.org/en/article/the-meaning-relevance-and-scope-of-energy-democ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