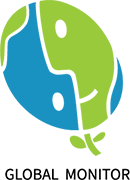2010年 1月 6日
Social Work After Baby P
Iain Ferguson 和Michael Lavalett主編,利物浦霍普大學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116頁,售價:英鎊5.95
回顧1970年代出現的激進社會工作學派,他們對貧窮和不平等現象(及其對兒童和家庭的不良影響)的分析具有較為清晰的社會和階級視野。這是由於1960-70年代英國正處於一個勞工階級戰鬥性較強的時期,那時比較多人認為:之所以出現各種社會弊病,病根在於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不公義。
可是,自從1980年代開始,新右派戴卓爾主義抬頭,推行極端的市場化政策,再加上1997年後執政的自稱奉行「第三條路線」的新工黨(New Labour)不但沒有叫停市場化,反而推波助瀾,令社會工作推動人權和社會公義的核心價值蒙上了厚重的陰影。社會工作流於追逐指標和禦防「爆case」,處於迷失方向的邊緣。這本小冊子針對這個惡劣趨勢,旨在提供有用的解毒劑,希望為社會工作的前景引發更多討論。
如何能夠挑戰兒童工作和家庭工作的「個人化」和「病理化」?如何挑戰把跟進這類個案的社工變成「替罪羊」的主流輿論?──這方面的討論一直很缺乏,尤其是與指向社會服務改革聯繫起來的討論就更少。小冊子的作者都呼籲需要重新發現久已被遺忘了的激進社會工作傳統,復興這個傳統,今天比過去任何時候顯得更有需要。
社會工作常常處於關懷弱勢和社會控制的矛盾中苦苦掙扎。這本小冊子呼喚一種建基於關懷和支持的新的社會工作手法,一種靈活的、機智不莽撞的和促進民眾抵抗的手法,每一位社福界同工和社工學生都值得參考。
既然小冊子是嘗試在新的時代重新引入進步社會工作傳統,因此,它的見解一定會見仁見智。不過,無論你同意還是反對它的意見,際此社會工作艱難時勢,有心的朋友將無法避免思考。
季耶根據網上介紹編寫
按:有關英國Baby P虐兒事件的背景介紹見https://globemonitor.org/zh-hant/content/%E8%8B%B1%E5%9C%8B%E9%80%B2%E6%AD%A5%E7%A4%BE%E5%B7%A5%E5%B0%8Dbaby-p%E4%BA%8B%E4%BB%B6%E5%9B%9E%E6%87%89
沉淪的社會工作?充滿希望的社會工作?
2009年 8月 12日
作者: 全球化監察
文/譚亮英 季耶
大澳社區工作隊社工謝世傑
就在社福界同工都關注基督教女青年會與民政局局長曾德成聯手壓迫大澳社區工作隊社工謝世傑事件的時候,台灣南部居民還受著颱風帶來的特大水災的磨難。雖然去年大澳雨災的規模不及今次台灣的,但兩地水災同樣揭示社區建設滯後和當局救援不力的問題。我們試想:假如過去大澳沒有像謝世傑一類熱誠的社工去協助居民爭取權益,你覺得這樣的大澳居民能否抵禦更大的災害?假如社工不作為,又或者社工站在政府和保守勢力一邊說服居民放棄爭取,以維護所謂「社區和諧」,你覺得這樣的社工是否稱職?
才不過十年 已面目全非
很多社福界同工不是不想發揮所學,而是社福界生態變化太大,而令其感到難以做好,寸步難行又深感壓抑。很多人已指出自2000年整筆撥款開始的一連串福利改惡的過程,政府和福利機構上層怎樣聯手把社會福利市場化和商品化,在資源增值的美名下怎樣一次又一次的削減福利,社會工作促進人權和社會公義的價值怎樣被肆意扭曲。這些都不必多說。
值得提出的是,看來政府不會對社福界實行全面的私有化,即不會全部出賣給商業機構,但是,政府計劃徹底改變社會服務的運作方式。一種充滿「小政府、大市場」的新右派思維的公共部門管治模式「新公共管理主義」(New Public Managerialism)90年代最初運用於英國,現在終於在香港登場。它認為只要公共部門「更好的管理」就能解決經濟和社會問題,而「更好的管理」的關鍵在於市場化。它強調量化績效(SQS….),把受眾塑造成消費者(錢跟老人走…),同時打造社福界的內部市場,要福利機構為合約和客源彼此競爭(服務競投…)。
最近,它更標榜「證據為本的實踐」(evidence-based practice)等「新方向」,進一步把福利服務帶到一個純技術官僚管理的「非政治化」的世界。它強調官商民伙伴關係(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甚至強調顧客參與諮詢機制(美其名曰「持份者充權」),但這樣卻把福利服務改造成「個人市場消費行為」。社會福利的社會公民權和民主問責的傳統受到嚴重侵蝕。
這樣的社會工作,由於被新右派思想主導的政府控制住,她將比過去更加無力處理日益嚴重的貧窮和社會排斥等問題,反而淪為協助權勢者粉飾太平的幫手:不加批判的推銷「社會和諧」;為那些極度剝削的大集團加冕(假如其覺得有幸一展關懷的話)、「好好生活運動」淪為叫基層苟活下去,而不去揭示造成市民艱苦的不平等的結構性原因;「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強調甄選申請項目的標準之一是「重視建立伙伴關係,強調商界及專業界別對社區的參與」,引導非牟利機構按商界的期望重組福利服務的意圖明顯不過。
在社福界幾乎面目全非的時候,國際社會工作者聯盟(IFSW)2000年通過的原則聲明是否有點恍如隔世?
「社會工作專業宣導社會變革,促進有關人類關係的問題解決並推動人們的增權和解放以增進福祉,通過運用關於人類行為和社會系統的理論,社會工作介入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人權和社會正義的原則是社會工作的基礎」。
「我們不是來幹這樣的社會工作的!」
今次事件揭示,至少自整筆過撥款推行開始,不到十年,社福界的生態便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權力更集中在政府官僚和社福機構上層中,而中基層同工普遍存在無力感,服務使用者被重構為「消費者」,在福利市場內購買已外判的服務。社福機構上層往往和政府深相結託,各得其所,而把社會工作平等公義的價值和基層權益都出賣掉。
整筆撥款推行已近十年,飽受蹂躪的社福界幸存下來,但她的功能差不多只剩下控制和監督,作為充滿關懷和增進大眾福祉的社會福利幾近消失。無疑社福界前景非常暗淡和悲觀。但是,在每個足以令人絕望的理由背後,我們要去尋找足以產生希望的理由。何況,有人已在尋找呢!
五年前,英國一群同工、服務使用者、社工學生和進步學者發起草根網絡「社會工作行動網絡」(Social Work Action Network),喊出「我們不是來幹這樣的社會工作的!」(I didn’t come into social work for this)並通過《社會工作與社會公義:呼籲新實踐的宣言》,期望凝聚力量,反擊社福界的市場化和管理主義改惡。本地同工會否借鑒外國的經驗,擺脫無力感,建立批判的、進步的和充滿希望的社會工作實踐,而不再是自覺迎合或被迫推銷統治階級設定的價值和政策?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21世紀的激進社會工作
2009年 5月 25日
tags: 激進社會工作, 社會工作
作者: 全球化監察
Iain Ferguson著,季耶 譯
按:文章原題‘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radical social work in the 21st century。刊於斯洛文尼亞社會工作期刊Socialno Delo,2006年,第45期,頁183-187。論文頭一節是談2005年卡特尼娜風災的意義,因與文章主旨關係不大,故翻譯時略去。作者Iain Ferguson是英國斯特靈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高級講師,著有《反思福利:批判的視角》(Rethinking Welfare: A Critical Perspective, Sage , 2002,合著)和《奪回社會工作:挑戰新自由主義與促進社會公義》(Reclaiming Social Work: Challenging Neo-Liberalism and Promoting Social Justice , Sage , 2008)。作者2009年5月底將出版新書《激進社會工作實務》(Radical social work in practice, Policy , 2009)。
是當前這種越來越不平等又失掉社會團結性的背景,使我們要再來談論社會工作的激進傳統的價值。這談論並不是為了懷舊,也不是妄想再現20世紀70年代的場景,而是因為社會工作的激進傳統對於社會工作的受助者在21世紀所感受到的不平等和壓迫最能夠給予關注和反對。
激進社會工作的傳統
正如Jones (1983)、Butler與 Drakeford (2001)的著作中所說的那樣,社會工作總是帶有一個激進的內核,帶有激進主義的傾向,甚至像19世紀英國的維多利亞慈善組織協會(Victorian Charity Organisation Society, COS)那樣是一個完全保守的組織也是如此。比如Susan Pedersen在一本為傑出的社會工作者、後來還成為下院議員的愛琳娜‧羅絲本(Eleanor Rathbone1872-1946)所寫的傳記裡,曾提到了羅伊登(Maude Royden1876-1956)。羅伊登像當時的很多志願者一樣,來自富有的家庭,於19世紀末期在利物浦的福利安置區(Settlement)工作了18個月:
她不輕易責備人家,她所遇到的一些事情足以讓 COS的理論家們大驚失色。一個碼頭工人的遺孀向她懺悔,自己已經把300英鎊的丈夫死亡撫恤金胡亂花得乾乾淨淨。羅伊登認為「她得到這唯一的機會這樣花錢,真是太好了!」那婦人一一說出她買了些什麼東西,他們兩個人「尖聲大笑」。
羅伊登顯然非常失望,福利安置區的理論和實踐根本就無力解決貧困問題。她承認自己
「就像白癡一樣,分不清什麼是值得,什麼是不值得的!」在她看來,這裡所有的婦女都「窮得無法形容」。她能夠理解為什麼他們整天喝的像酒鬼一樣。「貧窮、不幸的人兒!如果我住在蘭開斯特大街,我也會像他們那樣愛喝。」
在20世紀開頭,實行了社會工作教育的正規化,作為一種手段來防止友好訪問者被受助者的毛病傳染。這說明了:持有像羅伊登同樣觀點的人,不限於很少數(Jones, 1983)。
知道了這點,就毫不感覺奇怪,在激進傳統的大部分歷史中,它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只算是少數派的傳統。當它竟然出現的時候,大概就是正在經歷著巨大的社會變革,而且常常是響應更為廣泛的社會運動(Thompson, 2002)。比如Reisch 和 Andrews在其關於美國激進社會工作史的書中講到,一戰的爆發導致很多社會工作者湧現出來,最著名的有珍.阿當斯(Jane Addams,1860-1935),她積極參與了反對美國參戰的運動。20世紀30年代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和經濟的大蕭條,使得很多社會工作者參與了草根運動(Rank and File Movement);該運動的核心人物是馬克思主義者藍諾茲(Bertha Capen Reynolds1886-1978),它也積極支援工人的罷工鬥爭。在中美洲和拉丁美洲,巴西著名的教育家、哲學家保羅•弗萊雷(Paulo Freire)的思想深深影響了20世紀70年代的許多社會工作者。他們把社會工作當作是反對貧困、反抗獨裁、爭取社會正義的武器。最為有影響力的就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女權運動的興起以及歷時多年的民權運動和工會鬥爭使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的社會工作者認識到,社會工作的範圍不能僅限於針對個別的心理-社會個案,更要去探究受助者(client)問題的物質根源。有幾次激進的社會工作方式出現的原因,是對於那種往往令人覺得是太狹窄的大部分醫療性的社會工作感到不滿,是因為這樣的工作沒有做到既關注到受助者較大的生活環境,又充分地應對社會正義和社會變遷的問題。這種原因使人們想要有一種不同的社會工作。激進的社會工作對個案工作的批判,主要是個案工作把受助者以及他們的經歷都個人化和病理化,而忽視了與他們的問題有關的結構性因素。如此的著重點,在激進社會工作教科書的編者給激進社會工作所下的定義上反映了出來:
我們覺得,激進的社會工作,本質上是指我們要去瞭解受壓迫者在其生活的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位置。(Bailey and Brake, 1975)
當然激進社會工作還有其他方面的內涵,包括:對福利國家中壓迫者和統治者的批判;呼籲社會工作者與受助者之間建立友好的合作關係,不僅僅是在個人層面(這是在我們現有的受助者參與的方式之前就有的),而且還包括集體的組織層面;.強調通過集體方式來解決受助者的問題,如社區工作和社區行動,這在1980年代促成了諸如殘疾人運動的興起;它要求社會工作者要參與到工會中,和其他工人組織建立起聯繫,等等。不過,考慮到激進社會工作在21世紀的重要性,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關注社會環境,而不是強調一種新的工作方式。雖然早就應該在社會工作中更加強調集體方式,但是很多當代的激進社會工作者都同意Jan Fook的觀點,認為此外還有一系列的工作方式,包括個人的方式,也屬於激進性的。好的個案工作像社區工作一樣,也是監護制度主要的受害者之一。
我們強調社工關注社會環境主要有三個層面的意義:
第一,我們要認識到、並進而分析當前占主導的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是如何改變了實際社會工作的方方面面,不論它是像對待塞內加爾或哥倫比亞那樣,通過輸入結構調整計劃,還是像在英國及其他國家那樣,把社會公共事業逐步私有化,從而把社會工作者的作用變成監護人那樣(Ferguson, Lavalette and Whitmore, 2004)。John Harris (Harris, 2003) 和英國的 Chris Jones(Jones, 2004)為我們提供了這種分析很好的範例。
第二,我們要努力去研究造成受助者行為的原因。以前,瞭解受助者行為的原因一直是社會工作的中心內容(England, 1986)。然而後來,至少在英國,社會工作日益由深入向表面轉變了(Howe, 1996)。政府和社工管理層最為關心的不是去瞭解受助者的行為,而是通過對風險的評估和管理去控制受助者的行為(Parton, 1996)。許多所謂「有根有據」的做法都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把精神、政治和道德的問題化為「如何才有效」的技術問題,有關社會經濟不平等的大環境問題則刻意抹殺了(McIvor, 2004)
第三,通過社會環境來理解受助者就意味著,社會工作者需要挑戰和反抗官僚的權威,需要抨擊很多歐洲國家的政策,無論它是保守的還是所謂第三條道路的政策(Lavalette and Mooney, 1999)。比如, 1993年一名男童被另外兩名男童殺害,當時的英國首相馬卓安(John Major)就建議「我們需要少一點理解,多一份譴責」(引自Ferguson, 1994)。這種言論對民粹主義的政治是有利的,但對社會工作就非常有害。但是這種強調客戶至上、把受助者當做客戶的理念,反過來往往就是十分苛刻對待那些未能達到「合格客戶」標準的人群,主要就是尋求庇護的人、難民、青年人、心理健康有問題的人和貧窮的父母。社會工作作為一行職業,只有打算在這些問題上採取明確的立場,公開宣佈捍衛這些受壓迫群體的利益,正如國際社會工作者聯盟(IFSW)打算要做的那樣,我們自認是札根於社會正義的職業才不致成為空談。
總結
上世紀80年代,隨著共產主義政權的倒臺,美國國務院的研究員福山就宣稱「歷史終結了」,他的意思是說資本主義已經戰勝了它所有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敵人,從而戰爭、甚至局部戰爭都將終結(Fukuyama, 1992)。這一學說又被進行了後現代的潤色,認為再也不會有「大歷史記述」了,再也不能從整體上去理解世界了。但事實上大多數人都明白,在共產主義政權垮臺後,我們還看見過太多的歷史,不管那是1990年代在前南斯拉夫地區,還是現在的伊拉克戰爭,還是最近新奧爾良的災禍。很明顯,那些風行一時的關於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和「新美國世紀計畫」的新的大歷史記述,不管它們在其他方面做到了什麼,並沒有把這個界變得比較公正或和平。
但是我最後想說的是,殘酷只是現實的一個方面。在一方面,正是由於對新自由主義的強烈不滿,現在已經爆發了全球範圍的抵抗運動,其規模是自上世紀60年以來都沒見過的。全球抵抗運動起源於1999年反對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西雅圖會議,從那時起,這一運動就持續不斷地大規模開展起來,如,2005年在熱那亞、布拉格和蘇格蘭谷地進行的反對八國集團的示威遊行;在Porto Alegre 和 Mumbai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在佛羅倫斯和倫敦舉行的「歐洲社會論壇」。反資本主義運動或全球正義運動已經在挑戰新自由主義的主要信條,並且指責這種意識形態對全世界人民所造成的巨大損害。它的口號有「世界不是商品」、「另一個世界時可能的」。該運動已經在向世人昭示,我們可以按照公平、民主、多樣性和可持續性(justice, democracy, diversity and sustainability)這些理念來重新構建我們的世界(Ferguson, Lavalette and Mooney, 2002; Callinicos, 2003:112)。2003年2月15日,盛大的反對伊拉克戰爭的運動參加人數超過了一千萬,紐約時報稱之為「世界第二權力中心」(‘a second world power’)。在過去,社會工作中的激進運動往往是由於響應和加入這種社會運動而發展起來的(Thompson, 2002)。最後我要說:對新自由主義的社會工作的不滿,以及日益增強的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抗,無論是在社會工作的範圍之內還是之外,都可以幫助一種新的社會工作的方式或者新的世界觀發展起來,它能夠把傳統的社會工作裡面最好的成份與比較激進的結構性的工作方式融合起來,而它將成為比1970年代的激進社會工作更廣泛許多、也更強許多的國際性的運動。
參考書
Bailey, R. and Brake, M. (eds.) (1975) Radical Social Work, London: Edward Arnold
Bauman, Z. (2005)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2nd ed., Lond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Butler, I. and Drakeford, N. (2001) ‘Which Blair Project? Communitarianism, Social Authoritarianism and Social Work’,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 1, 7- 19
Callinicos, A. (2003) An Anti-Capitalist Manifesto, London: Polity
England, H. (1986) Social Work as Art: Making Sense for Good Practice, HarperCollins
Ferguson, I. (1994) ‘Containing the Crisis: crime and the Torie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62, 51-70.
Ferguson, I., Lavalette, M. and Mooney, G. (2002) Rethinking Welfare: a Critical Perspective, London: Sage
Ferguson, I., Lavalette, M. and Whitmore, E. (eds.) (2004) Globalisation, Global Justice and Social Work, London: 2004
Fook, J. (1993) Radical Casework: A Theory of Practice, Sydney: Allen and Unwin
Fukuyama, F. (1993)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Harris, J. (2003) The Social Work Business, London: Routledge.
Jones, C. (1983) State Social Work and the Working Class, Basingstoke: Macmillan
Jones, C. (2004) ‘The neo-liberal assault: voices from the front line of British social work’ in I. Ferguson, M. Lavalette and E. Whitmore (eds.) Globalisation, Global Justice and Social Work, London: Routledge
Lavalette, M. and Mooney, G. (1999) ‘New Labour, New Moralism: the welfare politics and ideology of New Labour under Tony Blair’,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85, 27-47
Lorenz, W. (2005) ‘Social Work and a New Social Order – Challenging Neo-liberalism’s Erosion of Solidarity’, Social Work and Society, 3, 1.
Parton, N. (1996) ‘Social work, risk and the ‘blaming system’ in Parton, N. (ed.) Social Theory, Social Change and Social Work, London: Routledge
Pederson, S. (2004) Eleanor Rathbone and the Politics of Consci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Reisch, M. and Andrews, J. (2002) The Road Not Taken: A history of radical social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Brunner-Routledge
Thompson, N. (2002)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work’,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2, 711-22
Save the Children (2005) State of the World’s Mothers Report 2005: The Power and Promise of Girls’ Education, New York: Save the Children
Swann, C (2005) “More Americans lack cover for ill-health” Financial Times Wednesday 31 August p.4
Wilkinson, R. (2005) The Impact of Inequality: How to make sick societies healthier, New York: the New Press.